走出技术垄断的美丽新世界
摘 要: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是一部著名的反乌托邦的批判小说,描绘了一个被高科技垄断且高度极权的未来社会。赫胥黎通过自己的想象描绘了一个被技术裹挟的新世界,人们在虚假的快乐中成为技术的奴隶,充满了对现实社会技术滥用的讽刺和批判。技术垄断时代使人们在媒介接触中逐渐形成不同程度的群体依赖与自我迷失,如果我们不能在技术所带来的舒适和娱乐中保持清醒,不能对其无限扩张趋势加以遏制的话,赫胥黎描绘的美丽新世界势必将会成为现实。我们必须重新倡导人文主义传统,注重公民教育的反思与回归,特别是具有批判性思维的媒介素养教育。
关键词:美丽新世界;技术垄断;媒介;教育
一、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由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在1931年创作的《美丽新世界》是二十世纪最经典的反乌托邦文学作品之一。反乌托邦是科幻文学中的一种文学体裁和流派,是相对于追求人人平等、按需分配的理想乌托邦而言的。在这种社会中,物质文明泛滥并凌驾于精神文明,精神文明依赖并受控于物质,在物质得到极大满足的掩饰下,人类文明在高度发达的社会被技术裹挟而失去了真正的自由。这类小说常通过描写技术的泛滥,揭示技术对原有优点的修饰,以及对固有缺陷的掩饰。技术的泛滥在表面上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而本质上是在掩饰空虚的精神世界。《美丽新世界》作为一部著名的反乌托邦的批判小说,描绘了一个被高科技垄断且高度极权的未来社会。
在这里,婴儿不需要母体孕育而是来自于“中央伦敦孵化及控制中心”,在他们还是胚胎时就被划定为α、β、γ、δ、ε五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与此同时未来的人生轨迹也被划定,而每个等级的生命设置就是沿着既定轨道行走。这就是世界国,他们标榜“社会、身份、稳定”,他们用睡眠暗示进行“许普诺斯教育”,用“新巴甫洛夫模式”扼杀喜好,唆麻是他们最有效的解忧方式。在世界国他们用“福帝”纪年并相信他才是唯一的神明。
世界国的人们尤其注重教育,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教育方式,但最主要的还是睡眠教育。从胚胎出生起就需要在午睡中接受各种启蒙教育,尽管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在听,更不可能理解自己听到的内容,但这些反复播送的信息对他们进行了洗脑式灌输,孩子的心灵总有一天会领会这些暗示。暗示的总和就是心灵的全部,而且是成人的心灵,这将贯穿他的一生,心灵的所有判断、向往和决定都取决于这些暗示。除了通过睡眠暗示,管理员们还擅长使用“新巴甫洛夫模式”,即利用条件反射的原理来重新定义人们将会感兴趣的事物,例如书本和噪音,玫瑰花和电击,通过大量的刺激性训练将这两组毫不相干的概念在孩子的心里形成密不可分的印象,反应条件就这样不可逆转地形成了。极权者所担心的是个体一旦有了感觉,社会就会发生动摇。为了保持稳定,所有条件设定的目标都是:让人们热爱他们无法逃避的社会使命。此外,他们还要学会把死亡当作理所当然的事。
除了这个世界国,列宁娜和伯纳德到访的保留地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里依旧是传统社会的村落,虽然没有先进的技术但人们整天都十分快乐地工作而且是全身心的快乐。这里的婴儿靠母乳哺育,这里的旧衣修满了补丁,这里的人们有自己的喜怒哀乐,这里没有人可以属于多余的一个人……但这看似正常的一切却让来自新世界的列宁娜感到恶心,眼前的一切与幼时接受的睡眠教育截然相反,她为正在哺育的女子感到羞耻、对衰老的相貌感到不可思议、对野蛮人约翰既反感又好奇。在这片技术还未曾染指的区域,人们靠双手而不是机器来进行生产活动,他们拥有文明,他们在这里歌唱、读莎士比亚、拥有属于自己的自由。尽管如此,从新世界过来的人们依旧执着于技术为他们带来的满足感,琳达就是一个典型的悲剧,她被抛弃在保留地但却由于儿时根深蒂固的教育让她已经成为了一个没有自我的躯体,她只记得睡眠教育的歌谣却不懂得在讲些什么又为什么会是那样,她宁愿重返新世界也不愿在保留地凋零,最终她在唆麻带来的虚幻快感中走向死亡。
二、媒介镜像与群体依赖
赫胥黎笔中的“美丽新世界”,不是社会为人服务,而是人的存在为了服务于社会。为了适应社会,人们失去了自己甚至失去了人性,变成了一个个服务于技术的技术复制品。这里的教育也不是为了唤醒个人,而是为了适应社会,利用教育来束缚个性,让人们乖乖顺从并热爱他们无法逃避的社会使命。自我被泯灭,思想被控制,生活在新世界的人们没有自我、没有感情,因而也没有理由会产生矛盾,在一片祥和的外表下,这个新世界事实上并不美丽——这正是赫胥黎想要警告我们的。
技术的发展为社会各个领域带来不同程度的机遇和挑战,对媒介来说更是如此。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媒介使用的手段,而媒介使用手段又决定了信息的传播。依托于技术发展的媒介在技术垄断时代必然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人们在媒介接触中逐渐形成不同程度的群体依赖与自我迷失,我们常常无意识地沉迷其中而忘记自己的存在。媒介企图在人际化传播的镜像世界中制造出一种高度模拟现实的交互方式。倘若我们在这种高度仿真中失去判断力,那么谣言传播和网络暴力等由于不实信息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将愈演愈烈。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每个人都是社会化关系中的一员,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和评价都来自于群体中的社会化交往。在这种陌生环境的交往中需要通过参照他人的行为来判断自己该怎样作出反应,我们时常因害怕被同伴排挤或被群体孤立而放弃自我立场倾向于顺应别人的选择。这种迫于压力下作出的选择是天然自我保护意识和对群体顺从的结果,也是造成占据意见环境优势地位的舆论形成的直接原因。当媒介作为社会的镜子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更愿意去相信媒介是代表了技术也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便毫不犹豫地做出顺从的反应。李普曼在《舆论学》中曾指出“媒介构造社会认识”,当我们在这种无意识中习惯了这种压力对我们行为的改变时就会失去对认同体的质疑精神,我们被这种莫名的信赖所麻醉。正如麦克卢汉的观点,我们被自己建构的媒介所吸引,爱上了媒介那充满梦幻的“倒影”成了自恋的那喀索斯。事实上,这种群体依赖是对媒介也即对技术的过度信任。尼尔·波兹曼认为,“向科学求助、对科学抱有期望、未经质疑就接受科学针对这些问题作出的回答等,都是科学至上主义的做法,是技术垄断时代的一个华丽的幻象”。
李普曼的“拟态环境”说已经在提示我们所处的媒介环境与现实有很大不同。我们面对媒介这面镜子时看到的像是不同于真实的自我和现实的环境,然而由于它所反映的像太过“拟真”使我们误以为它所反映的一切都是真实。作为个体的我们就像《楚门的世界》里的主人公,他的整个人生就是电影公司默默进行拍摄的一部电视剧,摄影棚就是他的整个世界而他却对此浑然不觉。虽然我们并没有楚门那样可怜,但我们必须承认媒介所营造的镜像对我们的影响和改变远远比我们能够意识到的大得多,娱乐化的媒介使用体验正在逐步吞噬我们的判断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也是楚门,我们的生活处处离不开媒介的控制,媒介营造的环境反过来作用于我们所处的现实环境成为新的环境,即拟态环境的环境化。
 |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 评论
- 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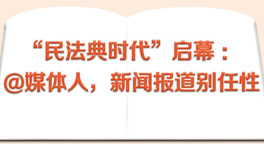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