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环境下的突发事件传播机制分析——基于第三人效果的维度【2】
4 转发消息的预测变量

研究者将转发消息这一第三人后续行为作为因变量,如前文所述同样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前四层的自变量不变,第五层的自变量是对微博的第三人感知、对消息的第三人感知和其他人转发消息的行为。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表7所见。
在第二次回归中,使用微博时长表现出了预测力。在第三次回归中,受教育程度、事件卷入度和人际传播进入回归方程。而第五次回归的结果表明受众对消息的第三人感知对于转发消息来说是一个显著的预测变量。因此H3得到了验证:由受众的第三人感知可以预测他们转发消息的行为。其他人转发消息也是具有预测力的自变量,这表示,如果受众觉得其他人会转发消息,那么自己转发消息的行为也会更加频繁。H6得到了验证。
5 抵制周子瑜的预测变量

在第二层的媒体变量中,使用微博时长对抵制周子瑜的意向有预测力。而在与信息有关的变量中,由事件卷入度、人际传播可以预测受众抵制周子瑜的意愿。在第五阶层中,对消息的第三人感知和其他人抵制周子瑜这两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即由受众对消息的第三人感知和设想中其他人抵制周子瑜的意愿可以预测他们抵制周子瑜的意愿。因此,H4和H7得到支持。
6 抵制JYP的预测变量

在第一次回归中,受教育程度进入回归方程。在第二阶层中,使用微博时长对抵制JYP来说是显著的预测变量。在第三阶层的信息变量中,事件卷入度和信息显著性进入回归方程。在第五次回归方程中,受众对消息的第三人感知和设想中他人抵制JYP的行为都是显著的预测变量。这说明,对第三人感知越强的受众,抵制JYP的意愿就越弱;设想中他人抵制JYP的意愿越强烈,自己抵制JYP的意愿就越强。因此,H5和H8成立。
在本文中第三人后续行为包括三个方面:转发信息、抵制周子瑜、抵制JYP公司,H16主张受教育程度与第三人后续行为显著相关,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受众的受教育程度只能部分地解释第三人后续行为。它对于转发消息和抵制JYP公司来说是显著的预测变量,但对于抵制周子瑜的行为来说预测力并不显著,因此H16只能说是部分成立。
五、结论与思考
综上所述,研究者对本文的研究假设的回答总结如下:

1第三人效果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稳定强大的认知偏差
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受众对网络的第三人感知这个因素之后,受众对消息的第三人感知依然表现出了对后续行为有着较强的预测力:不仅能够预测对微博的第三人感知,还能预测第三人后续行为如转发消息、抵制周子瑜和抵制JYP公司。这说明第三人感知及后续行为确实是由消息的传播引起的而非网络媒体所造成的影响。
研究还发现,无论有没有接触过消息,受众都会认为自己比他人较少地受到消息的鼓动,并且总的来说都认为自己比他人更多地受到微博的正面影响。这证明了第三人效果的普遍存在。
2信息的社会期望值、消息可信度和第三人感知间没有必然联系
社会期望值的高分组、中立组与低分组都对消息产生第三人感知,说明社会期望值与消息的第三人感知关系不显著。通过多元回归分析也发现社会期望值不能预测消息的第三人感知。消息可信度也不能预测第三人感知。这与过去文献测量的结果有较大差异。研究者认为出现这一结果与本次研究中选取的事件与民族主义情绪相关。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消息,尽管过于偏激,但其负面影响不如过去研究中的暴力、色情信息这么显而易见且影响深远,比起负面评价,民族主义信息涉及更多的事可信与否、属实与否的争议性评价。另一方面的解释是,在本研究中研究者要求受访者通过分别回答被激发起抵制情绪的频率来评估自己和他人所受影响,而不是直接询问受访者自己和他人所受的负面影响有多大,因此,尽管受众可能认为含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消息不符合社会期望,内容也未必可信,但这些因素都未必能够显著到足以预测受众的这种自我—他人差异。这也给了研究者启示,在研究不同类型的信息时,变量的表现会根据类型所涉及的现实情况不同。
3人际交流对于第三人效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预测变量
值得一提的是,从对第三人感知及其后续行为的多元回归分析可知,受众接触消息的频率和人际交流的预测力都是比较显著的。这说明尽管在网络传播的时代,人际交流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人际交流对于受众对消息的第三人感知和转发消息都有显著的预测力,而平时阅读点击搜索事件的频率却没有表现出预测力。可见事件的卷入度没有对第三人感知和后续行为有显著的影响,而人
际交流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预测变量,即越少和他人讨论新闻事件,第三人效果就越强大。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受众做了更多认知上的努力,他们对自身和他人所受影响的感知程度越大,同时自我-他人对比也随之缩小。因此,越多接触新闻信息,越多与人交流讨论,会使受众获得更多的认知,这种感知偏差是有可能减弱的。相反,越少接触越少讨论,第三人感知偏差可能会被强化,从而助长受众对公共舆论的错误估计。最终受众可能或被驱使在公共场合发言;也可能出于对被孤立的恐惧而保留意见或放弃自己的立场以迎合设想中的主流意见,便出现了沉默的螺旋。无论如何,人际交流仍在网络传播的时代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禹卫华.中国大众媒介信息流程中的第三人效果研究[D].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2]郑素侠.网络环境中的“第三人效果”:社会距离与认知偏差[J].新闻大学,2008.1.
[3]杨莉明.网络传播中的第三人效果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4]禹卫华,张国良.传播学在中国30年:效果研究的反思与进路——以“第三人效果理论”研究为例[J].国际新闻界,2008.
[5]Davison, W. P. The third-person effect in communication [J].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83, 47.
 |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推荐阅读
相关新闻
- 评论
- 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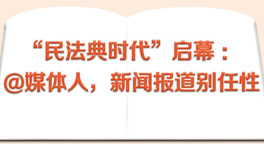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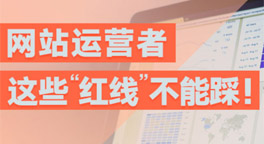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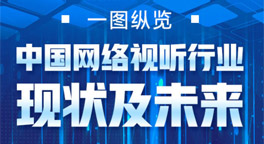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