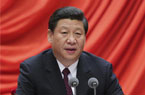三、 互联互通的美好新世界?
19世纪中期,法国一位典型的启蒙派学者舍瓦利耶(M. Chevalier)曾经这样阐述当时迅速崛起的交通和传播技术:“民主问题是一个依赖技术与工业发展的可变量。新传播技术和交通网的拓展不仅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而且减少了阶级之间的差距。因此这些技术的发展必定是制造平等和实行民主”。
可以想见,在工业革命的亢奋状态下,将平等和民主问题与新传播技术的发展勾连在一起的声音绝不在少数,但是像舍瓦利耶这样认为新技术会自然带来平等、民主、甚至阶级消除的言论还是多少有些震颤人心。然而,令人遗憾的是,19世纪中后期的历史并没有像这位圣西门追随者所预想的那样发展。尤其是世纪之交的年代,我们见证的是巨型垄断公司的崛起、资本对社会和文化的强力支配、金融与军事力量的迅速膨胀和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萎缩,所有这些对平等和民主不利的结果恰恰都是以新传播技术的发展为条件的。最终,在20世纪的前半期,我们看到了几个国际经济领域霸权争夺者之间的血战和一场人民的灾难,两次工业革命时期的雄心壮志变成了“西方文明的衰落”和一派号称客观、实证的保守知识气候。
历史喜欢重演,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市场的拓展让人们迅速忘记了20世纪所经历的一切。如今,美国的知识界又冒出一位敢说大话的媒体宠儿,这位叫托马斯?弗里德曼(T. Friedman)的评论家试图为还没有展开面貌的21世纪写一本“未来简史”,题目就叫做《世界是平的》。在书中,他列举了“碾平世界的10大动力”,几乎其中所有的“动力”都与新媒体传播技术直接相关。在这些动力的推动下,舍瓦利耶在19世纪所设想的美好新世界图景又原画复现了。更重要的是,弗里德曼先生的惶惶大著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畅销书,他书中的精彩故事和清晰论述折服了亿万读者。
《世界是平的》以及其他乐此不疲地鼓噪传播技术和全球化的论述能够如此流行,绝不是偶然的。它说明当今的都市中产阶级正在无意识地重温19世纪进步主义的梦想。此时,如果将他们拉回20世纪历史的放映间,敲打他们的美好理想,不仅显得过于残酷,而且很有可能得到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的传播效果。
我们在此放弃耸人听闻的预言,不暗示任何历史可能发生的结果,不去做弗里德曼言论的反面,只是希望能够挖掘这种技术决定未来的分析思路的逻辑和盲点是什么,希望以此为基础对互联网时代做出一些更为稳妥和审慎的判断。
首先我们想审视这个“未来”的概念,互联网像许多其他新技术一样,甫一出现就立刻被贴上“未来”的标签。但是,为什么会有“未来”?谁需要有“未来”?欧洲的启蒙现代性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它的核心要素就是“未来”比“现在”好的时间概念和不断积累、增长、进步的概念。到今天,这已经成为知识分子们呼吸的空气,怀疑“未来”的问题可能显得非常怪异。
20世纪50年代,罗兰·巴特(R. Barthes)在分析神话学的时候,曾将资产阶级当作“匿名社会”来谈论。他的意思是一个特殊利益披上了普遍利益的外衣而又不被察觉。这正是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的直接内涵。在互联网和全球化带来“平的世界”这套说辞的背后,也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匿名社会”,一个是资本力量,一个是国际政治霸权力量。资本的力量需要投资“未来”,“未来”是被资本许诺永远不会最终交割的巨大信用。在一个资本所组织起的社会关系中,每一个本不需要什么“未来”的普通百姓都被迫在“未来”上下注,却又都在战争和经济危机的赌局终盘上破产。新技术是“未来”的化身,必须将它神话才有“未来”。于是,资本不断裹挟人们的获利期待在每一代新技术上下注,鼓噪每一代新技术的发展将带来革命性变化。在传播领域,从铁路、航运、海底电缆、无线电报、电话再到今天的互联网,新媒体技术不仅本身成为资本投机的噱头,而且承担着支撑“未来”的重要使命。
在对互联网等新媒体的讨论中,将这些技术看作是自生自发的进步力量是一种普遍观念。但是如果没有资本力量的主导,这种转型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如果不是互联网企业拥有巨大的吸金能力,能够以高额的资金搭建基础设施和吸引人才,那么报纸等传统媒体是不会简单地因为一个新传播技术的出现而丧失人才、丢失广告,进而走向衰亡的。所以这种媒体转型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不是技术,而是资本。换句话说,技术的“未来”是资本的许诺和施舍。也正因为如此,至少在资本主义迄今的历史上,技术的发展还没能超越资本力量的控制,真正“社会化”的技术从未获得有效发展。如今的互联网企业,拥有巨大的资源聚拢能力,不仅逐渐垄断信息内容的生产,而且横跨网络金融和数据业务咨询等多个行业:一方面,凭借技术优势,很多互联网企业本身就已经成为一个金融投资集团,他们的政治经济操纵能力极强;另一方面,互联网企业所掌握的海量数据由社会个体行为汇总而成,为实施商业监控和政治监控提供了最便利的条件。以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与互联网企业的合作为例,这个政府机构每年用于从谷歌(Google)和微软(Microsoft)等高科技公司收集信息的项目就耗资近3亿美元,它向我们展示了信息产业领域的跨国集团和美国军政力量之间的紧密关系。
这个现象正引出了我们所说的第二个“匿名社会”,就是以主权国家为依托的国际霸权力量。任何互联互通的自由沟通都需要有个统一的技术标准,没有这个标准,只能是封建割据的状态,不可能发生畅通的传播活动和资本的大规模积累。在19世纪,这种技术标准可能是铁路轨道之间的距离,在20世纪则可能是电报电话和互联网等的通讯标准。在当今国际社会,谁掌握了关键传播技术的标准,并用强大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加以保护,谁就掌握了支配力,谁就能成为国际体系的核心力量,谁也就自然会不遗余力地倡导打破国家壁垒、促进信息自由流动和自由贸易。因为在这个自由传播的游戏中,标准制定者总是最容易获益的一方。我们将这种制定标准的“匿名社会”称作国际政治中的霸权力量。如今,对网络自由的倡导和推崇最为卖力的当然是在互联网技术上占有绝对领先优势,能够制定最重要的技术标准,并掌握最多终端服务器的国家——美国。
但是,我们特别想要提醒的是,这种技术霸权并不稳定。随着资本和技术从发达国家逐渐流向发展中国家,国际政治中的新兴力量随时会崛起。这就像17到20世纪,国际霸权从荷兰到英格兰再到美国的转移,标准的制定者可能因为国力的衰弱而让渡权力。在19世纪晚期,各个主要工业化国家都试图在第三世界推广自己版本的铁路、通讯等技术标准,这个过程与对殖民地的争夺和传播网络的争夺同步展开,而20世纪初期的两次世界大战,很大程度上就是欧洲内部各主权国家间争夺霸权席位的激烈化表现。当我们谈论互联网所容纳的多样化表达和充分互动的时候,如果脱离开这个背后的技术标准问题,以及掌握技术标准的“匿名社会”问题,那就只能是“不识庐山真面目”了。更有甚者,第三世界国家中很多知识分子打着所谓冲破主权壁垒、倡导互联网言论自由和争取民主平等的口号,实际上却很可能是助长了霸权力量的反民主和反平等的技术支配权力。
统一的技术标准、强大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垄断资本的推动力量,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互联网这种新媒体天生就不带有自治和多样化的基因。而正像前文所述,那些将互联网言论平台看作开放平等的市民社会议政平台,认为网络消费空间带来自由意志解放和更多公众权利的观点,必须建立在一种赛博空间与社会空间的二分法之上,即必须将网络空间的政治讨论与真实社会空间中的文化状态、阶层分化等问题隔绝开来。可是没有哪个网民不是带着真实社会身份和真实社会建构的文化意识进入赛博空间的,因此,这种抽象的分割显然无法成立。
因此,互联网政治有没有民主前景的问题,并不能在现有的技术条件和现有的社会文化中去讨论,否则我们永远无法跳出资本和政治霸权这两个“匿名社会”所设定的窠臼。要解决互联网民主的问题,必须发动社会力量从根本上改造技术形态和知识产权体系,创造一种“社会性技术”,一种充分自治的、没有支配结构的技术。与此同时,通过文化教化和对消费文化的对抗,改造社会的消极政治状态,重塑社会的公共性精神,并将这种精神带入赛博空间的公共讨论中。如果这两个条件遥不可及,我们就要重新讨论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问题,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要求基于国家间平等的传播权力。总之,改造互联网政治的基础,是改造社会,而不是改造技术。(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