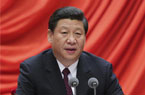摘 要:电影在跨文化传播中承担着生产和输出国家形象的重要任务。本文通过对20世纪60、70年代香港功夫片以及李小龙的一系列功夫电影中民族形象塑造的特点的归纳和总结,分析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形象在以欧美为代表的世界市场中的建构以及产生的跨时代国际影响。
关键词:中国形象;欧美市场;中国功夫片
与报纸、电视、网络一样,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影也在跨文化传播中承担着生产和输出国家形象的重要任务。而作为向欧美市场输出量领先的中国功夫片,也是在国际语境中表现中国文化,建构“中国形象”最具代表性的影片样态。
一、电影传播在国家形象建构中的地位
1.国家形象。学术界对于国家形象的一般定义是指“在一个交流传播愈益频繁的时代,一个国家的外部公众、国际舆论和内部公众对国家各个方面(如历史文化、现实政治、经济实力、国家地位、伦理价值导向等)的主观印象和总体评价”[1]。“内部公众”涉及国家民对于自身现实的整体性认知,而“外部公众”以及“国际舆论”则是国家的自身样态在国际化的语境中的呈现。可以说,国家形象并不局限于认识主体对国家历史与现实的客观反映。对于一个国家在国际视域下的整体印象以及得到的总体评价更包含了“主观”化选择、设计、构建、传播和塑造的过程。可以说,国家形象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完成的。
2.电影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作为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国家文化形象是一个国家经济和政治形象的有力支撑,对国家的形象具有巨大的提升作用和重要价值。而在影视文化产业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最具群众基础的影视文化无疑也负担起了塑造和确立国家文化形象,推动国民精神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命。相较于传播过程更为大众化、平民化和商业化的电视艺术,电影作为一个独立的媒介在国际传播交流中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电影诉诸视听语言符号的特性摆脱了传统媒介如报纸、书籍乃至广播对于单一符码(文字或者声音)的依赖。各国的电影创作者利用电影多重的符号结构承载了本民族的文化内涵,将电影作为媒介向世界展示本民族独有的文化特色,从而在国际范围塑造出本民族和国家的形象。“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凭借跨越语言文字不同所引起的‘传播阻隔’与交流困难的优势,成为当今社会最受欢迎的大众文化娱乐形式,在全世界拥有为数众多的观众群体。[1]”在20世纪60、70年代,一批带有强烈东方文化特色的中国功夫片、武侠片迅速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中蔓延开来,随之影响了欧美电影市场对于中国的形象认知。
可以说,功夫片对于中国形象在欧美文化时域中的建构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欧美市场占据了最大市场份额的中国功夫片,则以由邵氏影业出品的一系列武侠电影和由李小龙主演的动作影片为代表。
二、邵氏武侠功夫片:“文化中国”的形象自塑
邵氏影业萌芽于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后因历史原因迁移至香港。可以说,邵氏出品的一系列影片都潜移默化收到了海派文化的浸淫。邵氏影片发行所面对的主要观众群体是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等地区的华侨华人。历史上与大陆的文化渊源和华人为主的受众群体特质决定了邵氏影片的“大中华”属性。邵氏出品的电影作品注重对民族性的深层挖掘以及对中国传统的道德与精神理念的弘扬。“‘中国梦、民族情’是邵氏影片的核心内容。[2]”在艺术创作理念上,邵氏的功夫武侠片继承并发展了中国早期武侠电影传统, 同时借鉴了国际化的好莱坞式戏剧元素,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功夫片艺术体系。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邵氏的武侠功夫电影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为邵氏最为成功的电影类型。影片中所承载的“文化中国”的核心思想,在凸显影片民族气质,向世界展示东方传统武侠文化的同时,也对于构建中国形象起到了决定性的地位。
1.文人气度与暴力美学的缔造。作为邵氏新武侠类型电影的开创者,胡金铨的电影作品在追求视觉美感的同时也着力展现了中国文化中儒雅、冷静的一面。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胡金铨在电影中融入了舞蹈、音乐、戏剧的美学特质,并在营造符合民族传统的美学意境的同时学习了日本武士电影和美国西部片中制造紧张气氛的的创作精髓。从胡金铨的代表作《大醉侠》、《龙门客栈》和《侠女》中我们不难看出,胡金铨作品中的武打场面既包含了舞蹈的飘渺写意,也融合了京剧的利落真实。正如台湾影评家黄建业所言:“正是通过胡金铨的努力独创,‘原本粗糙’的中国武侠电影在《大醉侠》和《龙门客栈》中,让人目睹‘热血刚强的侠客鹰扬飞舞的身影后有着血汗熔铸的真情烈性’, 从此,武侠电影有了它‘在文化艺术视野中的深度和广度’。[3]”胡金铨的武侠电影中不仅有江湖儿女的刀光剑影,也不缺乏书卷气和文学底蕴。电影中侠士的身份,多半不是江湖草莽,而是文武兼修的人物。无论是外表扮相,还是言谈举止,都流露出儒雅的文人气质,使得影片的风格乐而不摇,文采风流,韵味十足。
与胡金铨强调文人化的艺术品格所不同的是,在另一位武侠导演张彻的电影中,草莽英雄的豪迈义气是影片所极力展现的重点。张彻的作品着力于强调男儿情谊,、男性豪气。这种“血气方刚”的气质直接地体现在影片激情浪漫、酣畅淋漓的暴力美学之中。在外形塑造上,赤膊上阵是张彻电影中英雄在决斗时的最大特征,古铜色的肌肤,结实的肌肉极大地彰显了主人公的男性魅力与个人力量。在动作设计上,为了塑造男主人公健康硬朗的形象,影片中的武打动作充满硬桥硬马的写实感,注重营造血脉喷张的暴力效果和紧张气氛的营造。在剧情设置上,张彻突破性地摆脱传统华人电影中“大团圆”结局式的故事架构,正面突出地表现以往电影所禁忌的惨烈打斗,强调死亡的震撼。影片中的桀骜的主人公在暴力的杀戮之后往往是以悲剧收场,这种独具特色的“暴力美学”开创了武侠影片故事架构的新纪元,并深刻影响了90年代以吴宇森为代表的香港导演的动作破案创作。除了张彻与胡金铨,而另一位武侠片导演楚原着力于将武侠文学大师古龙的文学作品搬上银幕。利用绚丽的光影视觉效果复原古龙文字中所描写的奇崛意境。楚原自觉地将唯美情趣与文艺气氛融入电影中,以个人化浪漫唯美的特点自成一格。
2.道德理想与现实功利的交织。胡金铨电影中的侠客代表了他所推崇的儒家文化中“仁”的特质。影片中的主要人物使用武力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完成自身保家卫国的崇高理想或是忠孝节义的道德诉求。影片中渗透着胡金铨本人对于武侠精与“以暴制暴”行为的个人反思。与张彻在电影中极力渲染暴力的主张不同,胡金铨的武侠电影中重视的不是力量的大力宣泄,而是技巧的写意化展示,打斗的场面多是点到为止,兼有舞蹈轻盈的美感。胡金铨塑造的侠客从容淡定的文人风范也是导演自身气质和人格理想在影片中的投射。而《侠女》作为胡金铨武侠作品的巅峰,使胡金铨的创作主题从对如儒道精神的宣扬逐渐走入对禅意的解读,使其作品在文学意味、历史积淀之外又具有了佛家的哲理。而对于香港武侠电影来说,除了拍摄技巧和艺术上的成就,胡金栓也是第一位将女性从充满阳刚的武侠世界中凸显出来的导演。在胡金铨的影片中出现的多个具有现代独立品格的女侠形象,是对以男性为主导的传统武侠模式的全新挑战。在同时期张彻的电影作品中,铁骨铮铮的江湖硬汉一改过去黄飞鸿电影中的正直保守的封建家长形象。在弘扬传统家国观念的同时,张彻影片中的主人公更注重对个人价值和自身尊严的维护。他们孤傲愤世,重视兄弟情义,“士为知己者死”是贯穿张彻影片的强烈感情,“以暴制暴”则是他们反抗世界,对抗所有不公的手段。张彻一扫之前香港电影的阴柔之气,呈现给世界观众一个纯“男性化”的江湖,女性在张彻的电影中多是以被保护的形象出现。而不同于胡金铨影片中所塑造的充满传统古典韵味的文人侠客形象,张彻塑造更多的是年轻气盛、快意恩仇,带有现实的功利主义色彩的现代英雄。
3.复杂人性与黑暗社会的呈现。在胡金铨和张彻电影作品中,人物角色模式是典型的正邪二元对立。而另一位武侠片导演楚原则注重利用影片挖掘社会的阴暗面与人性的复杂性。因此,影片中的人物多是正邪难分、亦正亦邪的人物形象。而这种打破了传统脸谱化范式的人物创作深刻地影响了香港后期以《无间道》为代表的黑帮片。楚原影片多翻拍自古龙的武侠小说,与原著中那些失望于人性却又坚守人性孤独侠客一样,楚原影片中的侠客无论行事多么乖张,仍然保留一份赤子之心、侠义之情。楚原影片中的江湖充满了争权夺利、尔虞我诈,这其实就是现实社会的缩影。脱胎于古龙原著的楚留香、陆小凤等带有传奇色彩的侠客更多的寄托了当代人的人格与理想,更蕴含着楚原本人对深陷时代困境的现代人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与思考。邵氏电影中的英雄侠客虽然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但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那就是他们只能够凭借个人力量与邪恶势力抗衡。政府要么是无能不作为, 要么是作为英雄侠客的敌对面出现。影片主人公多是“漂泊”于江湖的英雄的孤单侠客,而过客对家国的眷恋,也成为了以胡金铨为代表的邵氏“新功夫—武侠”影片的精神内核,以此来表现华人对于“文化寻根”的焦虑与渴望。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