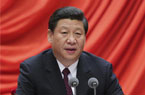赵玉明,这位生于旧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古稀老人习惯称自己为“十七年一代”的知识分子。“十七年”,正是这段浓缩了一个时代苦乐的特殊历史时期,造就了那一代人的集体面孔:乐于服从,甘于牺牲,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他们对工作有着炽烈的事业心,对国家有着强烈的责任感。更重要的是,他们受缚于时代,又感恩于时代。在他们的个体命运中,映衬着家国命运的流变轨迹,烙刻着历史造就的集体情怀。简单地说,他们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的信徒。
“我们这代人的特点就是服从分配”
1936年,赵玉明生于山西汾阳的一个农村,父亲早年在天津经商,40年代初,全家人迁往了天津。“到天津大概是1942年,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我是在天津上的中小学。我的小学过去叫天津私立第一小学,现在这学校已经没了。初中也是一所私立中学,叫通澜中学,然后考上了公立的天津三中。三中是一所百年老校,当时在红桥区铃铛阁。我在天津住过的几个地方,基本上都是围绕着鼓楼,先在南门里,再在东门里,最后在北门里。现在我们家的旧址找不着了,初中也找不着了,高中还有,但不在铃铛阁,已经迁新址了。”时至今日,赵玉明对天津的许多地界都记忆犹新、如数家珍,“我的中小学都在那儿念的,我可以算半个天津人了。”
因为父亲生病的缘故,没过几年,家人又从天津搬回了老家,只留下赵玉明一人在天津上学,直至1955年高中毕业。“高中毕业的时候准备报考大学,我当时学习还可以,文科理科都凑合,我们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希望大家学文科,所以我就报了中文系。”因为老师的影响,赵玉明一口气填报了北大中文系、南开中文系和北师大中文系三个志愿,并最终被北大中文系顺利录取。谁知报到以后,赵玉明很快又面临一个抉择:“北大中文系有三个专业,文学、语言、新闻,我们必须再报专业。当时我第一不知道新闻专业学什么,第二觉得自己一嘴天津话,语言专业肯定不行,所以我报的是文学专业,但最后我还是被分给了新闻专业。”说到这里,赵玉明非常感慨,“我们这代人的特点就是这样,让干啥干啥,让到哪儿到哪儿,大家都服从分配。就这样,我成了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55级2班的学生。”
赵玉明对在北大求学的那段经历记忆犹新,“当年北大中文系大概招了200多人,新闻专业一共3个班,一个班30多人,占了将近一半。那时候我们的老师有甘惜分、方汉奇、张隆栋、郑兴东、何梓华,还有去年去世的罗列。1958年6月,北大新闻专业和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罗列老师带着我们全体师生从北大燕园搬到了铁狮子胡同1号,也就是早先人大在城内的校址,现在叫张自忠路。”赵玉明说,“因为人大新闻系1955年招收了第一届学生,我们在北大也是1955年入学,所以1959年,我们又成为人民大学新闻系的第一届毕业生。”特殊的年代造就特殊的轨迹,从55级的北大新生到59届的人大校友,赵玉明的新闻求学之路折射的是新中国新闻学学科建设的坎坷缩影。他回忆说,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他们这批同学也收到了来自北大校友会的邀请,成为“北大加人大”校友,而能够得到两所著名学府的共同承认,他感到由衷的荣幸和自豪。
如果说北大的求学经历给赵玉明打下了新闻学史论基础的话,那么在人大所经历的则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和反思。“在人大印象比较深的是安岗老师,他当时是《人民日报》副总编兼新闻系主任,给我们讲新闻业务课。我们到人大时正赶上“大跃进”,课上得零零星星,主要就是实习。1958年夏天,我到当时还在天津的河北日报社实习,10月份又到了山西日报社,实习半年多后我们就面临毕业分配了。”
赵玉明继续说道:“那时候毕业分配也可以填志愿,但我印象当中大家的第一志愿都是服从分配,没有人在第一志愿中说我要上哪儿,只是在第二、第三志愿才填自己的想法。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最后会去哪儿,等待分配的时间是最难熬的。” 1959年夏天,一辆大轿车把包括赵玉明在内的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十几个大学毕业生拉到了他们未来的工作地点——一座五层的灰楼、两个篮球场大的院子,这就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刚刚兴办的北京广播学院,旧址在复兴门外,现已改建为中国广播电视音像资料部。也正是从这里开始,赵玉明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教学人生悄悄地拉开了大幕。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