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聞特征理論的當代發展【2】
三、新聞場與新聞的場域
新聞場是西方學者分析權力控制新聞、影響受眾的特殊概念,由法國學者皮埃爾·布迪厄(Bourdieu Pierre)在上個世紀90年代提出,認為新聞是社會各種關系和環境的產物,每條新聞難以擺脫場域性。“新聞場”(journalistic neld)是一個“具有自身規律的微觀世界”,“生產出來的新聞將特有的政治視角強加給公眾,而政治視角則根深蒂固地存在於新聞場的結構和記者身上。”[21]重要新聞是社會關系,特別是政治關系事件,總是出現在具體場合、具體地點。“從分析角度看,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各種位置的客觀關系所形成的網絡,或稱一個架構。這些位置和它們強加給處於特定地位的人或機構的決定因素,被不同類型的權力(或資本)所界定,佔有這些權力就意味著把持了這一場域的專門利益,也表明它們的實際和潛在的處境,以及它們與其他位置之間的客觀關系——支配關系、屈從關系、同源關系,等等。”[22]
這一論斷頗為費解,實際是說,新聞場作為社會結構的一種空間,由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形成恆定、持久的不平等關系。產生於不同空間(位置)的新聞總是由處於統治地位的力量——政府權力和資本權力所決定的,因為他們總要對一切社會關系與社會問題作出說明,維護其有利的地位和特殊利益。從這一角度出發,布迪厄分析了以電視為代表的大眾傳媒怎樣從民主的非凡工具蛻變為壓迫的工具,充當維護現存秩序的手段,“行使了一種特別有害的象征性暴力,這是一種通過施加者與承受者的合謀和默契而施加的一種暴力,雙方通常都意識不到自己是在施行或在承受。”[23]“象征暴力”看起來披上了“自願與自由”的外衣,實質貫穿強行支配的“場域”機制。新聞不僅在這裡產生,而且新聞的說服與欺騙也變得自然而然。
權力與受眾、權力與媒體的支配關系構成新聞的社會場域,受眾需求又形成新聞的報道場域。到20世紀末,媒介搶佔受眾的競爭開始白熱化,各個媒體在新聞報道場中激烈角逐,報道有時迎合官方,有時取悅公眾,商業因素造成強大的信息流,新聞由追求文化品位轉向迎合觀眾趣味。“各電視台越來越求助於轟動性報刊使用過的老掉牙的手段,雖不是把整個位置,但把首要位置讓給了社會新聞和體育消息。新聞場的特殊性在於,比其他文化生產場,如數學場、文學場、法律場、科學場等等,更受外部力量的鉗制。它直接受需求的支配,也許比政治場還更加受市場和公眾的控制。”[23]
西方權力階層的內訌和媒體口味向權力和公眾兩個天平傾斜,導致傳播內容的污名化和娛樂化,推動了新聞報道場域的低俗化。布迪厄認為,相對於文化生產的其他領域,如司法、文學、藝術或科學,新聞界同樣擁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權,但決定報道內容和形式通常需要這樣的社會條件——權力和公眾都喜歡的新聞才能既在當權者那裡找到靠山,也能讓廣大公眾津津樂道。於是在新聞報道場域盛行操縱新聞的手法是:“對事件進行掩飾,理順其中的頭緒,去掉其政治色彩,或渲染軼聞趣事和丑聞”。布迪厄繼而寫道:“大家都知道這樣的‘規則’,如果報紙或其他媒介想擴大覆蓋面,就得磨光棱角,排除任何可能分化或排斥讀者的因素。”[24]因為新聞報道場比科學場、藝術場甚至司法場更受制於市場邏輯的裁決。
新聞場最終體現為新聞話語場,大眾文化話語佔據主流地位。話語和話語方式實質就是說什麼和怎麼說,傳媒樂此不疲地尋找話題,把大眾吸引到它的話語場。當政治、司法、科學、文學、藝術等領域的專家人物在媒體上與公眾對話,這些“快思手”(fast-thinkers)喜歡用大眾詞匯制造新聞氣氛和民主氣氛,吸引公眾傾聽他們的調侃。布迪厄指出,一個文化生產者越自主,越有專業資本,競爭對手就失去了顧客市場。與之相反,越把自己的話語投向大眾,就越傾向於外部權力,如國家、教會、黨派互斗,就可能屈從於它們的要求或指揮。“這些‘電視快思手’、記者、史學家、辭典編纂家或靠錄音機對當代思想進行總結的人,都毫無顧忌地利用社會學——他們理解的社會學——在知識場四處出擊,發動獨特意義的‘政變’。”[25]作為思想競爭的場所,新聞媒體一旦用大眾話語提出新議題,就佔據了主導地位,等同於一場思想政變的成功。
美國學者A•克萊因把新聞報道場視為智力場的純理性領域,這裡充滿能知、想知、已知及語言的復雜關系,有知識的人才能如魚得水。他認為,新聞是最重要的文化話語,驅動人們的智力,使處於主導地位的修辭產生效果。新聞場告訴我們“誰能知,他知道什麼,是怎麼知道的,他如何建立和受眾的關系,借助語言如何構筑理性領域。新聞工作是一種理論實踐,而大多數記者沒有意識到這種作用。”[26]
克萊因進而對新聞場進行了總結,指出新聞場具有物理場的因素,正如結構偏差理論與敘事理論所揭示的那樣:“社會政治背景下的結構推出新聞產品,決定新聞實踐的效果。記者套用敘事結構,創建社會意識的連貫性和因果感,並形成時代的主導話語。”在他看來,新聞這個非封閉系統,傳達了這樣的純理性意義:(1)什麼可以知道和什麼不能知道﹔(2)能知道的問題的性質﹔(3)社會關系與認識者之間的性質﹔(4)新聞語言的內在意義與本質。 “換句話說,對於新聞場而言,(1)有什麼方法可以知道和怎麼知道﹔( 2)誰是知者,為什麼?(3)什麼是記者,他同事實來源和受眾之間的關系﹔(4)新聞語言如何創建這種關系,並提供新聞。”[26]就是說,新聞場這種權力和智力場所,充滿讓知和不讓知、能知和不能知的角力。
四、新聞是公共信息
公共性是新聞更重要的深層特征。塔奇曼在《做新聞》一書中認為:“新聞報道不僅賦予自然事件以公共事件的存在方式,而且還賦予其特征,因為新聞報道通過對事件特殊細節和‘特色’的選擇性披露,幫助公眾形成關於事件的定義。”[8]179丹尼爾·戴楊(Dayan,D.)與伊萊休·卡茨(Katz,E.)也認為:“人們每天從新聞接收大量信息,在接受、認知過程中必然與人們談論與自己生活圈子相關的新聞。新聞為人類生活提供了交流的話題,給人造成一種同情的思緒,隨之在大眾中流行。人們打電話聯系或互相走訪來評論事件,重新激活家庭紐帶和人們的友誼。”[27]新聞給人們提出的公共問題,讓許多人關心公共生活,這些新聞就成為社會公共事務的焦點。
許多西方學者強調,新聞不僅是大眾消費品,還是公共服務產品。新聞擴展公眾對身處環境的理解,滿足其監測環境的需要,把公共事件提出來讓受眾審視和交流。“雖然說,更多的受眾可能會選擇更簡單、更煽情的新聞,如來自電訊服務機構和廣播網的新聞報道,而不是選擇不太吸引人的、有關地方政府和商業的新聞報道。根據新聞模式,我們可以預測大量的新聞發現是積極的,或者說,至少在電視台能夠在承受成本基礎上報道積極的新聞,推進大眾對公共事務的討論和認識。”[28]西方的民主政治提倡,公民對社會政策要共同做出選擇,媒體提供的公共事務新聞便成為民眾選擇的前提,也是構建社會公共領域的基礎。新聞服務於民眾主要給人們提供精神指導,吸引他們參與公共事務,進入公共領域。而“公共領域本質上是由社會中的傳播機構組成的。事實和觀點在這些機構中流通,集體的政治性活動依賴信息共享。換句話說,這些傳播機構就是我們的大眾傳媒,為公民的自由傳播提供信息。”[29]
廣播電視新聞被經濟學家羅伯特·皮卡德(Picard, Robert G)稱為“公共商品”(Public Good),這種公共商品有下列性質:(一)它是公共產品,面向或供給每個受眾,價格低廉或無償供給,是保障政治生活正常進行的必不可少的公用事業。(二)新聞的質量並不完全決定新聞媒體的收益,新聞的吸引力決定媒體的利潤,在媒體和廣告商的眼裡新聞的收受率才是新聞的標准。[30]媒體把收受率作為新聞的最高標准,資本對新聞的支配作用便處於首要地位,這樣一來,媒體的公共服務職能不能不削弱,商業性能卻不斷增強。
為了充分實現媒體的民主功能,進而生成一個真正的“公共領域”,大眾傳媒“必須對所有公民開放,信息必須公開,對於那些可能會被信息左右的人而言,必須在制度上保障‘公共領域’的存在。”[31]反之,則要窒息公共生活的生機,正如英國學者霍華德·圖姆博(Howard Tumber)反思新聞及媒體喪失公共性所帶來的危險時指出的:“(1)新聞忽視了有效報道公共生活的責任﹔(2)這種失責必然引起公共生活的萎靡﹔(3)新聞應該而且可以成為振興公共生活的主要因素﹔(4)但前提條件是新聞業必須做出巨大改變。當然,我並不認為新聞業是唯一因素,普通大眾和政治家也應該做出貢獻。”[32]
 |  |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推薦閱讀
相關新聞
- 評論
- 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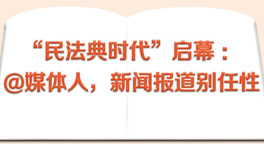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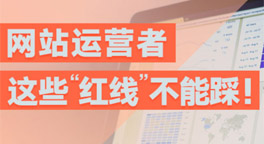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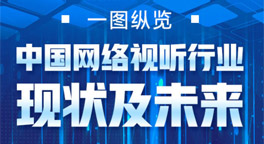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