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个人信息安全与挑战
——网络个人信息安全隐忧的成因研究
互联网技术时代,网络个人信息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一度使人们怀疑网络是否能够被规范。传统意义上,个人信息是指个人不愿向外透露的或是由于种种原因不想让他人知道的信息。在数字化时代里,个人信息的界定更为复杂,它包括生物体征信息、社会成员和社会文化信息等。相较于以往,这种界定将网络个人信息的识别度提高,能够更好地适应网络化、信息化时代,具有现实意义。
网络信息安全固然重要,但若是忽略了网络传播自身特性空谈重要性亦是毫无意义。网络社会的形成自有其内在逻辑,在网络社会中人们对安全这一概念的理解与传统也不完全一致;网络传播规律也对网络信息安全的保障增加了难度,更何况有着千差万别的网络个人信息安全。网络个人信息之所以存在很多安全隐患,法制层面、传播层面、文化层面都有原因。
一、法制层面的考察:网络法制建设滞后于网络发展 尽管目前没有针对网络个人信息安全的专门法,但是个人信息在网络上的各种流通形式在零散的一些法律条文中仍然能够找到一些可供探讨的东西。首先是关于传统意义上的隐私型定义的网络个人信息安全保障方面的法律规定。如《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第十八条:“不得在网络上散发恶意信息,冒用他人名义发出信息,侵犯他人隐私。”然后是关于通信自由和秘密方面的规定。比如,《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中第七条:“用户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利用国际互联网侵犯用户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五十八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电信网从事窃取或者破坏他人信息、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活动。”
除开上文已经提及的法律条文之外,部分省会还进行了地方性的法规尝试,如广东省2003年1月1日实施的《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2月1日实施的《广东省电子交易条例》,6月1日实施的《广东省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障管理规定》。以及北京市2002年10月1日实施的《北京市行政机关归集和公布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可见,广州市对的网络法制建设依然从公共的角度出发,这自然不容置喙,问题在于当政府把视线放在公共事务上的信息公开上时,对个人信息的保障便随之缺乏具有针对性的观照。此外,广东对于电子交易、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等领域的关注,在网络个人信息安全保障的关怀下略显狭隘。至于北京市的经验,则又局限于行政机关等,对于新兴媒体环境缺乏有益的探索。
二、传播层面的考察:网络传播造成的监管困难 信息不应仅作为一种资源存在,当然也不只是单方面的运行。信息传播的频繁流动本身即需要实时保护,其中更含有对信息建构之初,以及对信息传播后果的保护。而随着我国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融合的步伐,信息传播渠道正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呈现,而后对信息安全的理解又将随之升级、改变。
根据网络信息安全的动态性、复杂性等特征,不难看出,网络信息安全主要指信息的建构以不妨碍其他信息建构者及其行为为前提;信息的传播不受偶然或恶意的破坏、更改、泄漏;信息传播的后果有明晰的负责主体。故在三网融合、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等趋势下,网络传播规律仍然是开放的、流动的、交互的。
网络传播具有开放性、技术性。此外,全面数字化与交互性的web2.0时代,使得网络环境下个人信息保护呈现出新的特点。
网络环境的开放性使个人信息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首先,网络环境的开放为个人信息的集散提供了更广大的空间和技术条件,也客观上吸引了各种信息的流通。对于一些专门开发数据的公司或者数据库而言,搜集、存储、传播、分析个人信息越来越方便。其次,开放性给了许多不法之徒可乘之机,他们通过网络搜集他人信息、传播他人隐私,这种侵权行为给信息管制和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再次,在商业开发商上,开放的环境也提供了更加全面的数据资讯,这成为电商提供个性化服务的基础。
网络的技术性则造成了很大程度在代际上呈现难以逾越的鸿沟,对于那些掌握网络技术困难的人来说,其个人信息在网络环境中更容易受到侵害,一般社会公众和商家之间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即技术上的差距导致网络活动参与、表现、获取的不平等。而且,一些中介服务行为例如网络信息的搜索、浏览、缓存等,也会涉及个人信息侵权行为,而这些问题由于法律上的盲点无法进行准确的判断。
三、文化层面的考察:网络个人信息“公”“私”分际模糊 网络信息安全即便是延伸到集体、单位、组织等,指的也是一部分人内部共享的私密信息。然而隐私这个词汇进入我们的视野并非始于互联网时代,尽管诸多网络乱象的确让我们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更为警惕。早在20世纪末,大众媒介上已不乏以分享隐私作为卖点的例子。如1997年5月底,《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在第十版“人在旅途”开设了“口述实录”栏目。即便是现在,亦不难从报纸、广播电台、电视等媒介上发现“私密独白”“心灵倾诉”“相伴到黎明”,抑或“XX有约”“XX之约”的踪迹。受众面对素昧平生的记者、编辑、主持人,或侃侃而谈,或娓娓倾诉,大多数受众群体亦对此津津乐道。而这些无不是典型的私人话语。
然而与西方现代形成公领域和私领域,乃至隐私概念的缓慢历史不同,在中国形成的这种作为卖点,或者说为公众所分享的隐私文化是产生于一个急剧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的。在西方,隐私为人所普遍尊重和新闻传播有着密切关系,“黄色新闻”“新新闻”“钥匙孔新闻”激发了人们对新闻传播内容的反思,进一步促使了人们对隐私权力赋予法律保护的探索与思考。而中国的隐私文化更多地建立在大众文化消解精英文化的背景上,人们更关注个体自身,也对隐私话题扩张至大众传媒之上持更宽容的态度,并且这种态度最终将转化为收视率。这种某种程度上跳过了对“隐私”“隐私权”“自由”等话题的哲学思考,直接过渡到对个性的关注,形成泛滥的、暴露的、渴望被关注的隐私,便很容易引出“低俗化”的问题,也可能造成对他人个性的妨碍。
有学者这样认为,“公的东西就是见到的和观察到的东西,在观众面前表演的东西,公开给所有的人(或许多人)看到、听到或听说的东西;相反,私的东西是隐蔽的东西,在私下或私密或旨在有限范围人们中说的或做的东西。”[1]这或可被认为是对公领域和私领域的一个总体感觉上的描绘。它表明“公”和“私”的最大区别在于隐蔽性。如果将隐蔽性再加以褒贬描述,公的东西一方面可以促成舆论监督,另一方面又可能成为对人性的侵犯;私的东西一方面可以表达对人性的尊重,另一方面也可能成为对知情权的侵犯。
在哈贝马斯那里,“公共领域是对一切公民敞开的。私人性质的个体们每次聚集成公众群体交谈讨论,都形成公共领域的一部分。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像做生意谈业务那样,只关乎私人的事情,也不像宪政体成员那样,只服从国家官僚体制的制约。……在今天,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2]正如“公共领域”这个命名,哈贝马斯理想化地将“公共领域”赋予关注公共利益、公共事务的义务。如今的社交媒体上又有多少言论无愧于公共性的命名呢?故在此需要着重回答的是被规范、被引导的舆论对公共利益、公共生活又有何裨益?由此可见,真正推动网络立法的原因要到“公领域”中去寻找。
参考文献:
[1](英)约翰·B·汤普森著.高铣译.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61-262.
[2](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32.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 评论
- 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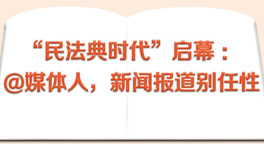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