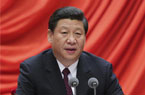摘 要:组建了银河映像之后的杜琪峰,影片风格逐渐统一并独树一帜,成为考察香港黑帮片体系的一个重要维度。其作品不仅在表层叙事上反映着香港现实社会的病态,更在文本深层与后现代美学特征不谋而合。审美日常生活化,在现实中表现荒诞、浓墨重彩地描绘人物复杂多变的精神世界这些元素在杜琪峰黑帮片中反复出现又不断翻新。本文旨在通过对包括《毒战》在内的一系列杜琪峰黑帮电影作品的本体研究,探讨其中蕴含的后现代美学意味。
关键词:杜琪峰;黑帮电影;后现代;文化
与许多香港导演凭借香港电影新浪潮引人注目,并创造了香港电影黄金年代的经历恰恰相反,杜琪峰在新浪潮如火如荼之时选择卧薪尝胆,而在香港影坛集体衰落的时候厚积薄发,成为香港电影一个不死的标志。他一边文艺一边黑帮在嬉笑与残酷之中自由行走,用爱情文艺片保证票房,用警匪黑帮片成为大师。远观杜琪峰的黑帮电影,是以类型电影为基床,师承黑泽明、胡金铨、梅尔维尔等电影大师的衣钵,再加以鲜明的个人特征,最终形成了冷峻黑色的“杜氏风格”。而当我们对其作品进行细读之后,却发现其黑帮作品中蕴含的文化内涵和美学走向极具后现代特征。当西方世界进入后工业社会以后,工业文明带来的危害与弊端也逐渐浮现,对工业文明负面效应的思考,孕育了后现代主义的萌发。后现代主义既是对现代主义的继承又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叛。它反对着一切简单的二元对立与既定规则,在种种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观念中,发现这些观念对人的压制与规训。由此衍生的后现代美学也逐渐成为了当今世界电影美学的一条重要的脉络,一个覆盖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的思潮。杜琪峰的黑帮电影虽然从未标榜过自己的后现代风格,但其作品却每每在影像间流动着浓郁的后现代气息,炫目的令人无法忽视。
一、审美日常生活化
当马塞尔·杜尚将一个男用小便池命名为《泉》匿名送往美国独立艺术家展要求展出时,已经宣告着一种崭新的审美时代的来临——高雅艺术、精英艺术渐次隐退,日常生活反而成了审美的主要内容。这种“反美学”正是后现代美学的基本特质之一,它的精神实质在于它不再承认有一个原本的存在(对本原、原本的追求实际只是一种形而上学),不再承认审美是生活的摹仿,而是强调生活与审美的同一[1]。换言之,后现代的美学特征之一就是将日常生活当成审美对象。
如果把吴宇森式的枪林弹雨与浪漫情怀当成黑帮片的标准,那么杜琪峰黑帮作品则多半不符合这种期待视野。他的影片中不但缺乏浓烈血腥的大场面枪战,就连主人公都不再是风流倜傥、重情重义具有完美人格的英雄。不仅如此,剑走偏锋的杜琪峰还偏爱通过表现主人公的日常生活来塑造反英雄形象。例如《夺命金》中,杜琪峰跳出自己的黑帮片惯例,首先将黑帮解构,再将其他两组看似毫不相干却又紧密相连的普通人捆绑在一起,三线并置。黑帮社团遭遇到衰退窘境,大佬大摆寿宴只是为了收礼金,却连荤菜也点不起;银行职员每天拼命工作却毫无业绩还要受到上司的指责;警察努力查案却无法满足老婆买房需求的尴尬,人物的日常生活、生存压力成为他表现的主要内容。而在其以往的黑帮片中,人物的日常生活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黑社会·龙城岁月》中任达华饰演的地区帮派大佬阿乐出场戏,在上海滩老歌《永远的微笑》的歌声伴随下,在菜市场买菜的他,身着最普通的休闲装,手提塑料袋,和颜悦色的让摊贩老板留两斤猪骨给他,说因为儿子喜欢吃。接下来就是阿乐在家中准备和儿子吃火锅的情景,正在吃饭的他接到成功获选“和联胜”新任话事人身份的消息时,虽是高兴却并未如老套的黑帮英雄那样肆意狂欢大笑,只是叫儿子多加了一支啤酒以示庆祝。这两场简短的戏与前几场戏的剑拔弩张氛围大相径庭,展示了地区大佬阿乐平凡却和睦的家庭生活。《文雀》开场亦有异曲同工之妙,任达华饰演的扒手阿祺自得其乐地在床边缝补着衣服,接着又将误飞入家中的鸟放生,然后骑着当代已经较为少见的自行车和其他扒手们汇合吃早餐。还有《放逐》中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五位兄弟,几年之后重逢在一起做饭、一起享用的场景。类似场景在《大事件》中亦有精彩的表现。
除此之外,几乎每一部杜琪峰作品中都会有一个不断进食的角色。很难说不停地吃东西这种角色特征具有太多深刻复杂的含义,更恰当的理解是,增加人物的日常生活习惯形成更为生动、立体的人物形象。虽然黑帮题材本身是极具戏剧性的,是超越生活、否定生活的,但杜琪峰将日常生活加入其中并将其审美化之举,便使生活与戏剧有机的融合起来,达到审美与生活的同一。这一系列对黑帮人物日常生活细致却不乏浪漫的描绘,展现出杜琪峰黑帮电影一个新的特质——将审美日常生活化。
后现代审美文化深刻意识到了传统美学的边缘界限对于美学和艺术在当代的发展的限制和障碍,并集中全力予以痛击[2]。杜琪峰正是借由后现代的美学观念,展开了对传统黑帮片的解构与改造。无论是反英雄的塑造还是对日常生活的审美,都是一种反传统的美学追求。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审美日常生活化的出现固然是对于传统的反抗,但却无法离开传统美学本身的存在。杜琪峰的作品亦是如此,其将审美日常生活化的做法,根本目的并不在于表现日常生活本身,而是试图创造反差,营造更为戏剧化的冲突。如《黑社会》中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其目的便在于营造阿乐这个人物性格的极大反差。一面是喜爱照顾家庭的慈父形象,一面是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的大佬形象,两者通过对其日常生活的描绘被有机的结合了起来。而《文雀》的日常生活展示就似乎更为后现代一些,因为整部影片的叙事都被日常生活的展示所缠绕。原本在传统偷盗电影中会出现的紧张气氛和精巧布局在这部电影中骤然消弭,取而代之的是略微神经质的故事和散文化的日常浪漫。
二、戏剧荒诞与现实荒诞
后现代思潮理论家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一文中指出,知识英雄为了高尚的伦理政治目的而奋斗,即为了宇宙的安宁而奋斗,这中叙事称之为元叙事即宏大叙事[3]。而所谓“后现代”就是对元叙事的怀疑。正因为质疑元叙事的合法性,于是解构元叙事成了后现代美学的特征。从表层叙事来看,杜琪峰电影所着力书写的仍然是老旧香港电影中钟爱的江湖恩怨、血雨腥风,然而,在其深层叙事中反常规的叙事却不断地反驳着传统电影的美学观念。银河映像成立之初,一种以杜琪峰为轴心的集体创作方式应运而生。伴随着这种头脑风暴式的创作方式,一系列充满实验前卫意识的黑帮作品如井喷般喷薄而出。同样是打破传统叙事模式,以分段式结构建构平行世界,《一个字头的诞生》比闻名世界的《罗拉快跑》更早地完成了对主流叙事惯例的挑战。电影从一直滴答滴答转动的手表开始,相同的开端,由于主角黄阿狗的不同选择而最终导致了全然不同的人生结局,而每一个选择之后的故事走向却都又饱含着人生无常的荒诞。整部电影荒诞到恐怖的场景莫过于在第一个故事中,黄阿狗一伙因赖账而挑起争斗后,在逃命的途中撞上了自己人大宝,而后在将大宝抬到家中抢救时,飘忽不定的昏黄灯光,晃动的手提式摄影,背景处传来的声嘶力竭的叫喊声,前景处大宝血肉模糊的脸和同伙惊慌失措的神情都将癫狂感渲染的淋漓尽致。突然间,大宝在同伙对其的心脏重击下惊醒,不仅口中梦呓般喊着不知由何而来的儿歌,还精神失常的手舞足蹈。就在已经如此让人不可思议的时刻,盲打误撞的大宝又将吊灯打破,整个场景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只有阳台漏进的一丝月光照亮了大宝模糊不清的脸。最终,大宝暴毙,荒诞气氛达到高潮甚至让人觉得毛骨悚然,生命的无常与荒谬被渲染到了极致。在后现代艺术中,所有的理性、常规与权威都遭到了高度的怀疑,而荒诞艺术则最能代表后现代美学的这一特质。它利用种种不合常理的形式呈现出一个非理性的荒诞世界,而构建这个世界的意义直指生命的荒诞。荒诞艺术永远以冷漠、旁观的态度来观察一切,它既不温和地批评,也不幽默地讽刺,只是展示着生命的尴尬。就像周而复始的推着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又像贝克特在《终局》中展示的人类终局,人类永远处在无法好好活着,却也无法安然死去的尴尬状态。《一个字头的诞生》在倒转的镜头中,将一切理性扬弃了。人物性格的神经质、摄影机运动的吊诡、幽蓝、暗红色调交错层叠、失焦镜头的大量使用达到了非理性与理性的极端分裂状态。杜琪峰用极尽夸张、荒诞的方式表现着生存处境的虚无和荒唐可悲与命运的不可控性。
如果说银河映像成立之初,杜琪峰在其作品呈现出怪诞乖张,极具实验意味的风格,那么不断突破自身又日渐成熟的他,在随后的作品中则更多的运用了纪实的方式。减弱了风格化的画面造型、没有了标志性的长镜头、摒弃了著名的红色血雾,《毒战》中有的是破旧混乱的城市、雾气霾霾的天、粗粝的影像与残酷的现实。但细观文本内部则会发现,荒诞却是杜琪峰依旧没有改变的表达诉求:“大聋小聋”看似与民工无异,却用人民币当作纸钱来祭拜嫂子;他们看似胆小怕事、忠厚老实,却不曾想一转眼就变成凶狠毒辣、招招毙命的神枪手,充满了黑色荒诞感。而《毒战》最能体现其荒诞性的还是结局的设置。英勇善战的警察与奸诈狡猾的毒贩在最后的斗争中居然全部覆没,而每个人的死去都充满了偶然和意外。虽然这是对《非常突然》结尾的直接移植,但由于影片一直贯彻的写实风格,以致“全部死光光”本就是超出期待视野的意外,到了本片中更显其荒诞性。而这种现实荒诞在《夺命金》中被演绎得更为突出,黑帮成员凸眼龙胸口插着一只金属花,在奄奄一息时还在等待股票的大跌,而三脚豹却记错了升跌还在期待股票大涨,两个一个喊升一个喊跌,这两个人的镜头不断互相交叉,看着股市由跌变升,也看着两人的表情变化,直至独眼龙毙命;普通老妇显然完全听不懂银行职员对基金问题的提问,但心中空有一张美好蓝图的她却重复地回答“清楚明白”。为了满足自己对金钱的欲望,影片中的每个人都在飞蛾扑火、乐此不疲。已经异化的人被金钱所统治、所驱使、所奴役,已经扭曲与畸形的人,在现实世界中更显得触目惊心。
三、从双重人格到精神分裂
如果我们细致地观察一下杜琪峰的诸多黑帮作品,会发现许多角色性格都具有明显的双重人格特征和双重人格情结。《暗花》结尾,梁朝伟为了逃脱追捕而假扮刘青云,却被对方发现,于是两人在废弃的房间中展开枪战。有趣的是,四处树立的镜子倒映出两人几乎一样的身影,甚至连他们自己都无法分辨。显然这正隐喻着正与邪其实只是一个人的两个侧面;《黑社会·龙城岁月》中的阿乐表面上为人谦和、慈爱稳重,俨然一个好兄弟、好父亲形象,却在争夺话事人身份时,用极其残酷的方法亲手杀掉了所有为他造成障碍的对手;又如《大块头有大智慧》结尾时,刘德华饰演的善良的大块头竟然与自己心中邪恶的心魔对战。影片意在指出,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至少双重的人格,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能否获得平静决定于一种人格是否能战胜另一种人格。如果说,前面的作品都是以侧面的方式探讨人的精神问题,那么到了《神探》则将全部精力都倾注在探讨人性和人的精神问题上。影片中几乎每个人都有双重以上的人格,而最大的罪犯竟然有7重人格,而主角陈桂斌本身亦患有精神分裂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杜琪峰对人性其实是有着深厚的兴趣和深入的探索的。在他的心中,人性的复杂程度远远超乎人们自身的想象。
这与后现代美学中有关“精神分裂症”的探讨殊途同归,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指出:“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种性格、野心和必然产生的幻觉,不可穷尽的疯癫就有多少种面孔”。因此,不存在疯癫,只存在着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拥有的某种特殊的性格、脾气或禀性,而且主要是“人在对自身的依恋中,通过自己的错觉而造成疯癫”[4-7]。 在福柯看来,所谓“疯癫”来源于理性话语中心制的确立,是自诩为理性主义者利用手中的话语权对其他与自己有差异群体的武断评判。《神探》当中:“如果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鬼,而只有你没有,那就是你的问题”这句对白,便是对该问题的直接映射。有病与否,往往与自身无关,而是需要依靠外界的评判标准而定。陈桂斌之所以被指为精神分裂,不过是因为他与平常人不同。他能够剥掉伪装看穿人性的真相,而大家还在为人性的伪装所蒙蔽,所以“当所有人都是疯子的时候,那个唯一的正常人会被认为是疯子”。后现代主义美学强调人性的差异性、不确定性和相对性,通过对整体性和同一性思维方式的拆解,回归人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于是,影片中出现了由7个迥然相异的形象来扮演一个具有7重人格的罪犯的7个侧面,在每当罪犯出现心理斗争时,7个人就会展现出不同的特点,而最终罪犯做出什么行为,取决于哪一种人格占上风。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在杜琪峰的电影世界中人性所具有的不可知性和模糊性是后现代美学的一种体现。
四、结 语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当代世界电影文化与美学整体趋向于后现代主义时,杜琪峰也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到这一世界性的思考当中。或者说,因为他生在当下的后现代语境中,所以在认识世界和自我时无可避免的附和了后现代主义的潮流。不过,无论他是否出于自觉意识,杜琪峰的作品都让世界对当代香港社会和现代人性有了更为丰富而深刻的认识。无论他拍摄的是戏剧化的黑帮故事,还是关注当下的社会生活,观众能从中看到的所有故事都关乎人心、关于人性的现实。
(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电影研究所)
参考文献:
[1] 刘悦笛.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日常生活化——试论“生活美学”何以可能?[J].哲学研究,2005(1).
[2] 潘知常.反美学的美学意义——在阐释中理解当代审美文化[J].哲学动态,1995(12).
[3] (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态[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 张之沧.走出疯癫话语——论福柯《疯癫与文明》[J].湖南社会科学,2004(6).
[5] (美)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精神[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6] (美)詹姆斯·纳雷摩尔著.徐展雄译.黑色电影:历史、批评与风格[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7] 徐向辉.杜琪峰电影的哲学解读[J].艺苑纵横,2004(2).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