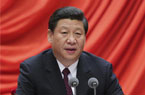摘 要:本文阐述了20世纪30年代初,在我国新闻舆论界兴起的“杂志年”浪潮的来龙去脉,通过从新闻方面、教育方面、国内外形势方面等对这股杂志热潮发生的历史背景进行多维度的分析,同时结合当今实际,得出要采取适度的把关政策,才能在维持我国新闻舆论界繁荣的同时又保证我国社会稳定、快速发展的结论。
关键词:杂志年;历史背景
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战场硝烟不断,法西斯主义凶残肆虐,整个国家处于剧烈动荡的崩溃边缘。新闻舆论界当然不能平静。其中,以《生活》周刊为代表的期刊杂志,更是以一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叱咤风云,载入史册。自1932年始,中国国内发展较早的沿海开放城市,期刊杂志在数量、种类等方面呈直线上升的增长趋势,这标志着30年代初杂志浪潮的开始。直到1935年,浪潮达到发展的巅峰。据统计,到1935年6月底,全国各省市杂志出版品种如下:
南京:187种 上海:398种 北平:150种
青岛:7种 江苏:127种 浙江:99种
安徽:11种 江西:9种 湖南:63种
山东:33种 湖北:78种 山西:43种
河南:43种 河北:131种 云南:10种
广东:44种 广西:7种 青海:1种
察哈尔:8种 贵州:4种 福建:23种
绥远:9种 甘肃:7种 陕西:7种
四川:17种 威海卫:2种
共计:1518种[1]
正是由于杂志期刊千树繁花似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从1932年到1935年,被时人称为“杂志年”。
林语堂先生曾说过:“杂志是一国文化进步的最佳标志。[2]”“杂志年”热潮当然成为推动当时的文明向前驶进的蒸汽火车头,而现今,在“十二五”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开端,对于“杂志年”的研究意义显得尤其重要。本文意在研究“杂志年”热潮发展的历史背景,以期寻找与当今时代相契合的历史结合点,为现阶段我国新闻舆论界的发展提供建议。
一、浪潮的历史大舞台
下文将分为五个方面,从多维度分析孕育此浪潮的历史背景,一探其登上历史大舞台的来龙去脉:
(一)中国新闻事业的成熟
1815年,第一家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在马六甲创办了,自此,中国新闻事业迈出近代化发展的步伐。之后,最先觉醒的一批国人在洋人所办的这些早期报纸影响下,认识到报刊杂志在国家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开始了探索自办报纸的实践。1874年,王韬于香港首办《循环日报》,成为我国第一位成功的办报人。梁启超先生更撰文《报馆有益于国事》,总结了报纸的重要作用:“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3],这一进步思想从此成为影响数代报人的金科玉律。在此坚厚的基础上,1919年,通过“五四”运动的激发,发起以《新青年》为首的新文化运动,确立了民主科学的办报理念,使新闻工作者的思维得到极大开阔。随后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申报》改革,也给我国的新闻工作者提供了重要的办报经验。到此,经过百余年的发展,踏着先辈们筑造的坚实阶梯,中国新闻事业已经初步达到成熟。
而杂志人,学会了经营理念上坚持受众本位,在管理上有意识、有套路地经营广告,注重发行量,实行多种经营,由此得以生根发芽。邹韬奋曾描述过在《生活》周刊社负责广告业务的徐伯昕的一段拉广告的情形:“伯昕先生每天夹着一个黑色皮包,里面藏着不少宣传的印刷品(这都是他一手包办的),他不但有十二万分的热诚,而且还有一副艺术家的本领,把宣传材料做得怪美丽,怪动人,东奔西跑,到各行家去用着‘苏张之舌’,尽游说怂恿的能事。[4]”
此外,《生活》周刊还“积极开发《生活》资源,充分利用<生活>周刊的热销效应,出版发行《生活》系列图书,实施多元化经营[4]”。
(二)争取出版自由斗争的胜利
民国时期,政府大肆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从1914年始,陆续颁布了《出版法》、《报纸条例》、《著作权法》等专门法,在国内形成了严酷的禁言法网。但同时新闻舆论界和民间的反对声音也随之此起彼伏,反抗运动一浪接一浪。在如此环境下,1930年12月,国民党政府还是不顾国民情绪,再次颁布《出版法》,“在全部的44条规定中,对报纸、杂志和书籍的出版、登记作出了十分苛刻的限定[5]”。中国新闻舆论界再次向国民党政府发起了大规模争取出版自由的反抗运动。1932年,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49家出版机构就联名反对《出版法》,要求保障新闻出版自由。最后,由于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国民党政府被迫向出版界让步,“同意对以前曾准予发行的书籍酌加删改继续发行。[5]”
在政府妥协的前提下,在一股拥护出版自由的风气中,虽然经营杂志的过程还是很艰苦,但是杂志还是迎来了发展良机。以《生活》周刊为例,从“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两年间,《生活》周刊在“印数达最高数15.5万份时,直接订户达5万户。其中外地订户3万多户,本地订户1万多户[4]”。
(三)中国国民文化水平上升
“杂志的荣枯,多数和文学史上的运动息息相关[2]”。30年代初的“杂志年”热潮根源在于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点燃了开发民智、培育人才的薪火,国民整体文化水平自此开始得到不断提高,为杂志的发展培植了肥沃的土壤。
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主要领导人将西方的教育思想引进了国内,促使这些当时的精英教育家突破传统教育思路的禁锢,激起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潮、职业教育思潮等多种崭新的教育思潮。其中,平民化教育思潮由于视角聚焦广大的普通民众而受到重视,是其中最重要的思潮之一。1916年、1919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分别通过了《注意贫民教育案》和《失学人民补习法》,我国教育事业走上了普及化教育的轨迹。该思潮以“要实现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必须打破等级制度和借机差别[6]”为主要观点,主张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只有获得丰富的知识,才能改变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红色革命根据地也在20年代末建起了教育系统,进行了广泛的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和儿童教育。这一系列的教育活动,不仅为我国发展近代教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而且有效地提高了根据地人民的知识文化水平。
经过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教育思潮,中国国民的知识文化水平持续上升,杂志的读者和编辑群得以不断扩大。以《生活》周刊为例,邹韬奋一直以为读者服务为信条,破天荒开办了《读者信箱》栏目,使《生活》周刊的编辑人员可以及时了解到读者的需求,及时与读者交流,有效地在互动中培养了热心追随的读者群,有部分读者如艾寒松、陶亢德、杜重远等还从热心读者摇身变成了《生活》周刊的撰稿人。
另外,除普及化教育外,专业化教育培养了大批专业型人才,其中以任鸿隽为代表的一大批科学家以《科学》杂志为基地,发起了“科学教育”思潮,提出“科学的教育化”和“教育的科学化[6]”,为专业性、学术性杂志的发展也提供了相应的读者和编辑群体,在杰出的教育科学文化界先辈们的努力下,《中国地质学会志》、《中国化学工业会会志》、《科学世界》、《中国物理学报》等杂志在学术界各领风骚,闪耀出文明进步的光芒。
(四)国民经济的衰退
1927年到1937年,“由于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的扩张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对国民经济的垄断、掠夺,以及国民党新军阀连年内战的破坏[7]”,中国的国民经济举步维艰。首先,表现在对民族工业的重挫,“以上海为例,1934年新设厂28家,改组291家,歇闭70家[7]”,由此可见萧条。其次,农村经济更是惨不忍睹,“逃生无路,水藻捞尽,草根掘尽,树皮剥尽……阖室自杀者,时有所闻,饿殍田野者,途中时见,……大小村落,鸡犬无声,耕牛绝迹[7]”。因此,大部分国民衣不果腹,书籍滞销,而杂志为了获得生存,销售价格普遍都定得很低,大部分只能勉强维持生计。但杂志又以丰富的信息量著称,如此一来,就以高性价比吸引了读者,获得夹缝生存。《生活》周刊创刊时,每份的售价是三个铜板,由于《生活》周刊的读者群主要是社会底层平民,所以纵使经营艰难,还是经过多次价格的修改,直到1932年,调整为“全年五十期连邮费一元五角,国外四元,零售每份三分五。香港、澳门、九龙二元五角。邮票代价九五折”。
(五)国内外战争硝烟不断
国际方面,为应对1929年经济危机,受灾国纷纷采取各种拯救措施,加紧对外的帝国主义殖民掠夺,谋求通过剥削殖民地来转嫁危机,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激烈的贸易战、关税战和货币战[8]”。日本和德国则选择把法西斯军国主义魔爪伸向了全世界,而对此,英、美等国均采取了绥靖政策,导致被侵略的国家无不为此做出了重大的牺牲,中国、埃塞俄比亚、西班牙等战场战况惨烈,国家和民族都面临瓦解的危险。国际战争局势随时变动,作为东方主战场的中国在必定与之息息相关,中国国民更是迫切需要第一时间了解抗战情况。而杂志,秉持受众本位,极力加大信息量,丰富每一期的内容,获得认可,取得发展。《生活》周刊的《读者信箱》栏目就特意针对现实战况,加强了与读者的互动,“大部分篇幅主要用于讨论抗日救亡的问题。[4]”
在国内战场,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民族、反正义政策,在明在暗开展剿灭共产党的活动。在明,分别在1931年和1933年发动了第四、第五两次杀伤力极强的围剿;在暗,“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两大鼎鼎有名的特务组织建立,开始在全国“疯狂而残忍地镇压一切革命活动和革命分子[7]”。
正是在此情形下,国共战火不断,战争局势和中国未来的命运也随之变化多端。其次,共产党主持创办《向导》、《布尔什维克》等杂志积极宣传“全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宣传机构进行激烈论战,也起到了促进杂志业发展的作用。再次,到此时为止,国内知识分子对于两党合作建立统一民主共和国的愿望彻底破碎,从而开始思考站队问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思路在思想文化界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因此,动荡的国内局势加以各种思想言论的及其丰富,坚持与读者紧密联系的杂志就得以形成强劲的发展浪潮。正是由于以上五方面历史背景,造就了这一场 “杂志年”浪潮。此浪潮深入到社会每一个兹待苏醒的角落,承担着宣传新知、唤醒民众的历史重任,在当时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林语堂先生所说的,“毋庸置疑,伴随着中国觉醒的历史的,是几家杂志和几位杰出报人的历史。[2]”
二、浪潮的黯然谢幕
“杂志年”浪潮在1935年达到顶峰之后,便猛然步向暗淡,渐渐淹没于历史长河。当时,国民党政府利用《出版法》等专门法建造起文化专制主义统治,还利用其“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组织对新闻界进步人士采取暗杀活动,以法律和法西斯暴力联合组成的白色恐怖,残忍地绞杀了这一场以杂志为主角的思想文化盛宴。例如:《生活》周刊在邹韬奋由于被国民党特务组织列入暗杀名单而被迫出逃海外后失去了灵魂人物,在喊出“统治者的利剑,可以断绝民众文字上的联系,而不能断绝精神意识上的联系。人类的全部历史记载着,民众利益,永远战胜了一切。一切对于民众呻吟呼喊的压抑,都是徒劳的[4]”后,于1933年被国民党当局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敏、毁谤党国”的无须有罪名查封。
其实,这一场“杂志年”浪潮本来就是在与国民党当局的不断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只是全靠众多不屈不挠的新闻战士怀着为民为国请命的崇高精神,不顾性命冲锋陷阵,杂志才得以艰难生存的。例如《太阳》月刊就曾因为不断地被查禁,在短短两年之间改了五次刊名,而鲁迅先生为了逃过审查制度,更是“在1933~1934年就用了60多个笔名,发表了200多篇杂文”[1]。但是,即使无数新闻战士用身躯筑造成的维护民主权利的血肉长城,最终还是挡不住只手遮天的权力和军队,这把锋利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最后还是斩断了中国新闻舆论界民主自由的根,“杂志年”浪潮只有在轰轰烈烈后,黯然地退下历史舞台。
三、结 语
上文在系统研究了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以1932年为开端,到1936年结束的“杂志年”浪潮的始末中看到,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拐点,思想文化界都会闪耀出无数智慧的繁星,但是,这些繁星最后都免不了在专制的打击中慢慢变得暗淡无光,最后被黑暗吞噬。读史是为了以史为鉴,通过历史的联想当今之中国不是也正处于历史转型期吗?由于各类新媒体的腾空出世,中国的文化界不是也正呈现出舆论大开放的态势吗?严禁还是宽松不也是我们正要思考的问题吗?由此,串联古今的众多历史结合点便跃于纸上。
现今,在新媒体塑造成的全媒体时代,公民可以通过移动媒介随时随地获取信息、发布实时信息和个人言论,且一经发布,马上呈现于全体公众眼前,真正实现了“全民记者”。但是,结合我国的实际,其中也有不利因素。在如此开放的媒介环境下,“把关人”的作用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新媒体塑造的这一个舆论环境就近似于是一个无管理、无秩序的环境,管理机构只能在各种不良微博已经在社会产生影响后,才能后知后觉地进行收拾残局性质的删除。这样绕过“把关人”的传播模式,也许很多人会认为是言论自由、是言论的解放、是值得提倡的。而经过上文对于“杂志年”的分析,似乎开放的舆论环境对于思想文化界的繁荣也是必要前提,似乎没有必要出现所谓的“把关人”,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讲:“审查官永远是世上最荒唐的职业。[2]”
但是,林老彼时所描述的“审查官”是代表着封建专制,而现在的管理机关是在社会主义民主领导下的监管机构。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即使是言论开放的西方国家,也不例外要实行严格的法律法规,对2011年的《世界新闻报》“窃听门”事件的审判就可以很好说明这一点。对于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很多方面的制度还不够完善,社会各层次中还存在着种种问题,关键是我国国民理性程度还不高,从为防核辐射而抢购食盐的事件、为保钓而上街打砸日本产品事件等群体性事件就可以窥探一二。因此,应当尽快召集新闻界、司法界等各界学者,制定出台正式正规的新闻出版专门法,完善媒体、尤其是互联网和新媒体的管理机制,培养出一批批高素质的专业管理人才,同时在大力推行公民素质教育的进程中,增加媒介素养的培养这一项,使其成为普及化的教育,再配合采取适度宽松的管理政策,做到既保护对我国社会发展有利的进步言论,疏通公众通过媒介监督政府的渠道,保证公众的监督和舆论权的同时,制止对社会有害的反动言论渗透到舆论环境中,进而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使我国可以在这一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不断前行。
(作者系:广西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 宋应离.中国期刊发展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
[2] 林语堂,刘小磊译.中国新闻舆论史[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3] 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4] 赵文.《生活》周刊与城市平民文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
[5] 黄镇伟.中国编辑出版史[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
[6] 张传燧.中国教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7] 王文泉,赵呈元.中国现代史[M].江苏:中国矿业学院出版社,1988.
[8] 齐涛.世界通史教程[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