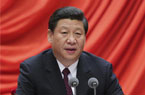摘 要:台湾因种种历史因素导致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形成了多重身份混淆的状态。王童作为台湾新电影时期成长起来的导演,他的电影映射出台湾居民对身份认同的困惑。作为台湾社会变革大潮中的一份子,在繁杂混沌的历史漩涡中,王童有逻辑地表达出个人在历史向度中对台湾身份由认同到认同崩塌之后的反思直至最终得以重建的历程。本文试图从“身份认同”理论角度出发对王童的电影进行研究,展示“身份认同”问题在其诸多作品中的显现,探求造成其身份认同困惑的历史、社会和心理原因,以期寻找一个能够使台湾人正视自己、消除身份困惑的出口。
关键词:王童;身份认同;主体建构
由于特殊的“历史遭遇”,台湾电影在诸多层面上呈现出一种纷繁复杂的文化特征。政治上的悬而未决导致台湾在政治身份、国族身份乃至文化身份上一直存在着非常强烈的身份认同危机。1895年电影面世,同年满清帝国战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台湾割让于日本,这个原始质朴的海岛值此踏上一条坎坷之路。较之于侯孝贤、杨德昌而言,台湾电影导演王童似乎鲜少被大陆观众所熟知,而作为台湾历史的见证人,经历过那个动荡年代的王童,在身份认同议题上却比同时期创作者思考得更深,走得更远。而从其早期作品《假如我是真的》、《苦恋》到“台湾历史三部曲”甚至到《红柿子》中,“身份问题”一直或隐性或显性的被反复讨论。
一、冷战思维下的政治身份认同
台湾的文化身份具有多元性和混杂性的特征,在身份认同问题中的焦点是如何看待他者和如何正视自己。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退居台湾,以“亲美反共”为主张进行意识形态宣传,这种典型的二元对立逻辑在坊间造成一种“台湾为中国主体”,而大陆则是受苦受难的同胞的政治想象。然而70年代末的“台美断交”和“中美建交”却直接导致台湾社会的集体心理恐慌,国民党鼓吹的“亲美反共”主张因为美国“联中抗苏”的态度而身陷囹圄。于是,为了巩固其身份建构,国民党继续实施着冷战思维下的政治策略“中国主体形象”。反映在宣传策略上,便是一来适度放宽有关台湾本土文化的书写与拍摄,借此来平复社会民众的心理失衡;二来积极筹拍揭露中共“问题”的政治影片。《假如我是真的》、《苦恋》便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诞生的作品。
《假如我是真的》是大陆作家沙叶新创作于70年代末的剧本,改编于当时上海市发生的一起冒充高干子弟招摇撞骗的真人真事。因为内容直指某些大陆官员官僚作风,批判意识强烈。所以一经公布就引起了轰动,最后还惊动了中共中央的高层领导,在一系列激烈的社会争论声中致使该剧禁演、禁拍。而该剧本流传到台湾后,却被认为是用来揭露大陆黑暗政治的有力武器,马上安排投拍。王童本出身于大陆,1949年后随家人来到台湾并进入国立艺传学习美术,由此进入中影。由于这样出身和经历确证了他在国民党体制内政治身份的,于是王童被定为拍摄该片的第一人选。而为了在体制内获得更充足的生存空间、取得导演的位置,王童也依中影指示适时筹拍了电影版《假如我是真的》。果然,《假如我是真的》很快获得了当时还由政府主办的第18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男主角、最佳改编剧本三项大奖。当国民党对现实中“反攻大陆”“复国还乡”的理想不被抱以希望后,只有对中共的臆想和讽刺得以保存精神上的力量。
《苦恋》是军旅作家白桦发表在1979年9月出版的《一月》第三期杂志上的电影剧本,后经长春电影制片厂批准,由导演彭宁拍摄成电影《太阳和人》,影片于1980年底完成。与《假如我是真的》相似,《苦恋》的故事改编自当代著名画家黄永玉的某段真实经历。这部由国营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批准拍摄的电影却在送审过程中遭到扣押,原因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和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认为此片违背了“四项基本原则”、丑化了党的形象。假如80年代初紧张的台海关系是《假如我是真的》获奖的必要条件的话,那这种政治裹挟下的艺术作品想必不是王童所追寻的。在电影《苦恋》中,王童在尊重原著的同时倾注了更多个人的思考。影片中响应政治号召的内容之外,也发出了台湾人民对自己身份的拷问——我是谁?我该如何做一个正确的自己?随着新中国在国际社会受到的广泛认可,国民党敏感的政治神经被触动,加大力度否认和丑化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这一不理智的举动导致台湾岛内初现的种族融合局面产生极大裂痕,原本由“中华民族”“华夏子孙”等历史共同记忆缔结的认同纽带发生断裂。台湾的国际孤儿地位激化了民众的心理恐慌,台湾人的政治身份开始瓦解,继而产生对国族身份的质疑与困惑。国民党在国族认同和身份认同上所显现出的排他性暴露出越来越多的潜在危机,为缓和社会矛盾,国民党逐步放宽对台湾在地文化表达的限制,以期找到稳固其根基的社会心理依据,于是才有了王童等一批导演所经历的新电影运动。
二、民主政治语境下的自体反思
自国民党入台到70年代末,台湾社会的政治身份认同是以国民党为中心的“中国主体形象”为主导,而文化认同则以“儒、释、道”为主的中国文化为主导。一直到80年代初期,台湾当局前后经历了一系列的内政困境(蒋家换代)和外交失利,国民党政权逐渐显出松动迹象。1983年以来,国民党无论是对于中国大陆还是日本,整齐划一的态度已经基本消失。一直到1987年台湾“解严”,这五年间台湾经历着身份蜕变带来的阵痛和反思,社会各界开始尝试运用新的思路面对生活,文化界通过对本土历史的梳理来寻求身份认同的答案。1983年间台湾共推出了10部新电影,象征着新电影风潮的全面来临。《小毕的故事》(陈坤厚)、《儿子的大玩偶》(侯孝贤)、《看海的日子》(王童)等一系列影片将台湾电影从半死不活的泥潭中拖出,掀开了台湾电影史的全新一页。
《看海的日子》这部电影讲述了妓女白梅从屈从于命运到活出自尊的完整经历。“焦雄屏在《台湾新电影》一书中有详尽的论述:‘(80年代)台湾面临物质及价值观的剧变,传统大家庭制度崩溃,小家庭林立,父权独占体系亦随之瓦解,女性大量步入社会。由此女性正面临角色抉择的仿徨,台湾电影此时大量引用文学小说的女性形象,尝试为过去女性角色的压抑及受苦下注脚,也反映出女性在社会变化下寻找新身份的努力’。 [1]” 影片虽在讲述妓女的悲惨生活,但也不乏鱼市兴隆、农民分到田地这样的“健康写实”片段。这可以被看作是王童在体制内生存的一种手段,然而电影的深层次主题依旧是对人物身份的探讨。影片中白梅的身份是缺失的:她从小被亲生父母寄养在别人家,十几岁又被养父被卖到妓院。养父去世,白梅以女儿的身份回家祭奠,却被兄弟姐妹们嫌弃排斥。这一经历摧毁了白梅作为养女的身份。自以为有了自己的孩子就能找到归属感的她,怀上身孕回到乡村老家,却发现生父已故、兄长残疾。白梅依靠自己顽强的毅力,带领家人过上了饱暖的日子。本以为一切都将幸福美好,但在白梅生产之时,还是因为孩子的身份问题在故事的结尾长吁短叹。像台湾这样一个不折不扣的父权社会,受严格的道德伦理和宗族观念影响,只有以父之名才能象征身份的确立。白梅的养父和生父都被导演安排为死亡,而孩子父亲的下落也被画上问号。虽然影片结尾洋溢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但也透露着寻找身份过程中的迷茫与艰辛。
如果说《看海的日子》是王童对体制内书写底层人物的尝试,以及对台湾身份焦虑的情绪化表达,那《策马入林》便是他对身份认同问题的深刻思考和个人风格的成熟展示。影片无论从故事架构、人物设置还是美术风格上都烙印了王童的印记。作为故事的主人公,何南是一个被土匪大哥收养长大的孤儿,同时从小受到后勤五叔的呵护,大哥、五叔这一父一母的安排构建出一个确立的身份认同。当土匪大哥骑劫了村民的女儿时,松散的土匪体系与紧凑的家庭体系产生抗衡。这种由家庭身份认同隐喻社会身份认同的艺术手法正是王童隐藏在本片中的深刻主题。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一切社会之中最古老而唯一自然的社会就是家庭,家庭是政治社会的原始模型,首领就是父亲的影子,人民就是孩子的影子。[2]”如故事所讲,土匪向村民勒索粮食,但因收成不好村民无法按数缴纳,土匪一气之下绑走了村民的女儿弹珠。十天之后土匪再次索要粮食,却遭到村民请来的官兵抵抗,土匪大哥被擒,人头落地。土匪体系中“父”的消失致使必须由“子”来稳固体系的身份认同,所以就有了影片中何南(养子)动怒强奸弹珠的这场戏。表面上来看这是“子”完成了成人礼,但依据拉康的“镜像理论”,主体的形成需要经历镜像阶段才能最终形成具有“想像界”“象征界”与“真实界”三个层次的主体结构。也就是说何南必须在一种父子关系中形成进化,蜕变为真正的“父”的地位。而在此影片中,何南始终面对的是如何看待自己的难题,他在弹珠眼中的形象便成了他的一种镜像——一个期待受家庭身份所认同的何南。如此说来,何南由“子”到“父”的成长并不是向土匪大哥的转变,而是逐渐脱离土匪体系、向家庭体系靠拢的过程。
当何南苦苦追寻弹珠,却被“爹派的人”从后面一枪刺死。这一刻与何南刺死乌面的影像极为相似,刺死乌面是雨夜天,象征着土匪体系身份的瓦解,也是何南身份认同的改变。这一次何南被刺,夕阳美好、树林寂静,是家庭体系的代表“爹”对何南的排斥,孤儿何南终究未能建构起自身的身份认同。说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出《策马入林》与《看海的日子》有一些相似之处。王童导演依旧在影片中寄托了个人对台湾的情愫。台湾这个国际孤儿,对中国、对日本、对国民政府都像是一段段纠葛于寄养与认亲之间的复杂关系。国民政府曾经口中的“中国”与当下中共执政的“中国”显然是两种身份认同下的产物,而台湾一直向往的(旧)中国,却在新中国得到国际认可的现实中被摧毁。《策马入林》是王童导演生涯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也是标榜个人风格的一座里程碑,它的意义不仅限于作品本身,王童因为这部电影开始将艺术的表达深入到台湾本土的骨髓,透晰台湾历史的筋脉,最终定将建立起包容博大、牢固可靠的身份认同观念。
大多数人知道王童都是通过他的“台湾历史三部曲”:《稻草人》、《香蕉天堂》、《无言的山丘》,这三部影片对半个多世纪的台湾历史展开了深切的反思,是他回归历史找寻身份的重要阶段。以电影《稻草人》为例,电影讲述了在台湾的日殖末期,佃农陈发、陈阔嘴两兄弟为了养活成群的孩子、耳聋的母亲和发疯的妹妹,背着炸弹向殖民政府邀功领赏的荒诞故事。导演用荒诞、戏谑的手法去演绎小人物的悲苦,真实再现了殖民时期台湾人民凄惨无奈的生活状态,同时对台湾文化中的日本形象进行了反思。黑格尔在总结“主仆辩证法”时写道:“它们在低级阶段是不平等的、对立的,尚未通过反思而达到统一,因此它们是以对立的意识形式显现的,一方面是自在的独立性,另一方面是依赖于他者的非独立性,这是本质。前者为主,后者为仆”[3]。也就是说,经过足够“反思”的主仆关系便可达到精神上的统一,仆人开始认可主人的身份及价值观,接受自己的地位和主人的施舍,从而退化为主体的影子并依附主体而存在。这便是日本皇民化运动所期望达到的目的。如影片中哥哥陈发得知“改叫日本名字可以换白糖”后,便放弃祖宗的传统;又如当得知“送去废铁可以得奖赏”后,陈氏兄弟承受生命之风险向日本军部讨赏,这些都是“仆”向“主”靠拢的具体体现。在影片结尾那一桌“其乐融融”的晚饭上,日本的战争、美国的炸弹还有地主的绝情都被陈氏兄弟当作善良的犒赏,这正是主仆关系的确证。晚饭中阿婆与孙子的旁白以及一家人高唱着日本军歌,都是导演对该时期台湾人对日本的复杂情感展开的戏谑、反讽的表达。
于全球化而言,身份的建立必须从台湾本土化中寻求答案,而放在台湾的本土历史中去看,家庭似乎是超越政治能够凝聚和包容时空变迁后各项因素的不二载体。《香蕉天堂》让我们看到王童具有包容性的对待台湾人的中国身份,这部作品以微观视角去表述家庭带给每一个成员的牢固的身份认同。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未知父亲”“父亲死亡”“外乡人”“寡妇/逃妻”这样的符号,这些符号的出现并非偶然,是王童在梳理个体与集体记忆中留下的历史伤痕。父权的衰落在对台湾身份的本土化探索中传达出巨大的伤痛,这既与威权体系离去所带来的恐慌感息息相关,又与台湾民众所感知的集体乡愁密不可分。在全球现代化的过程中,台湾社会的主体性遭受到挑战,所以对历史的怀旧表达中定不会缺少“失去父亲”的符号,这是社会变更时期的台湾集体记忆。所以归根结底,台湾的身份认同所遭遇的障碍便是政治体系崩塌后面临的父权体制的解构,如何建立稳固的家庭体系则是恢复台湾身份认同的症结所在,而这种家庭体系越来越多的指向父亲之外的多数家庭成员,更具包容性的看待每个人在家庭乃至社会中的地位与贡献。
三、逃脱政治后的主体建构
90年代由于美国重新制订了对台政策,台美关系趋向缓和。这一举措致使本就松散的台海关系更增添了错综复杂的态势。加之李登辉当政后提出的“台独”主张,两岸关系再次落入冰点。在这种背景下,90年代的台湾电影纷纷将眼光从遥远的历史中抽离出来,开始关注当下、关心自身。蔡明亮、何平、徐小明的相继涌现也在不断彰显着个人表达,成为90年代台湾新新电影的主要创作特征。也许是受到了社会环境的影响,又或是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感悟,这一阶段的导演王童似乎对政治左右的历史不再抱有探讨的兴趣,也不再纠缠于政党的功过是非,而是用去意识形态化的手法,从另一个角度解答在政治环境下人们如何找到精神寄托、如何建构身份认同。
在台海关系危机再一次爆发的1995年,53岁的王童拍摄了电影《红柿子》,这也是他知命之年里拍摄的第一部电影。王童以此片来呈现父辈人生的沧桑巨变,亦是他经历了三次深沉的反思之后,为迷宫般的身份认同困境找到的一个出口,给出的一个答案。影片《红柿子》以娓娓道来的方式讲述了关于一个家庭的记忆,故事的情节简单的用一句话几乎就能够概括,即描写1949年内战结束时,年迈的姥姥随着国民党将军女婿从大陆撤退到台湾之后的生活。鲜活生动的生活素材使影片充满了真实生活的质感,去意识形态化、回归普世价值的手法将历史隐匿于后景之中,家的意义从而强烈凸显,王童对家庭的留恋与回味不言自明。
影片中,姥姥的形象召唤出一代人的集体乡愁。姥姥的存在是对过去记忆的保留,而在她身上也映射着中国人对土地的依恋。乡愁一直是中国人举足轻重的情意结,以至于有人说过:“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乡愁”。所以,这种属于中国人式的特有的人文精神表征,得到了同一文化背景下族群的认同,两岸之间的族群差异顿时被消解了。家乡的那棵柿子树成为了她心心念念的存在,如同沦为“孤儿”与“弃儿”的台湾对与大陆的思念。另一方面,摆脱了对政治的苦苦探寻和之前王童作品中强烈的历史感,传统却充满着生活智慧的姥姥照顾孩子们洗澡理发、学习打架,一家人养鸡、养牛蛙都成了故事最华彩的部分。除了乡愁,影片在点滴琐事中还召唤出了我们对家庭的集体记忆。在《红柿子》的世界中,所有的困难都能在一个有姥姥和一大帮孩子的家庭中解决,所有的苦闷都能在家人的关怀下得到安慰。所谓家国、所谓天下在这里通通落实到了一家人的穿衣吃饭上,政治与历史仅仅成为生活的注脚。这部电影中的王童,终于摆脱了政治与历史的绑架,不再依附在政治立场与国族大义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是认识到自身作为主体,终于有了对身份的选择权利,而一直以来对于身份问题的不断思考,终于在这部电影中得出了答案——消除族群因政治背景不同而形成的差异,以个体为起点,通过共同的记忆与文化来建构的一种能够跨越差异性、更具有包容性的身份认同框架。
四、结 语
王童电影中所显现出的身份认同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他通过对政治、历史、社会和心理等几方面的梳理,逐渐打开了一条解决身份认同问题的出口——在承认中国人身份的前提下,正视历史,以家庭为中心有包容性的接纳不同文化间的交融,建构多元文明交织下的台湾人身份。“身份并非是一种界定或者归宿,而是对自身拥有的文化资源的不断开掘”[4]。王童的电影是为身份认同问题打开的一个出口而非一个固定的答案。在全球化趋同的当代,台湾本土化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这也将是台湾身份问题探讨的中心思想。如何平衡全球化与在地化对台湾的影响应是下一步研究台湾身份问题的入口。希望生活在每一寸土地上的人民能够力所能及地减少历史和政治带来的困扰,充实、愉悦地迎接新的未来。
(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 电影研究所)
参考文献:
[1] 陈飞宝.台湾电影史话[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
[2] 刘骋.身份认同与想象中的台湾新新电影[J].当代电影,2011(4).
[3] 范捷平.论瓦尔泽与卡夫卡的文学关系[J].当代外国文学,2005 (4).
[4] 吕红.海外新移民女作家的边缘写作及文化身份透视[J].华文文学,2007(78).
[5] 陈飞宝.台湾电影史话(修订本)[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
[6] 黄仁.电影与政治宣传:政策电影研究[M].台湾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
[7] 焦雄屏.台湾新电影[M].台北: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88.
[8] 李道新.中国电影文化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9] 王海洲.镜像与文化—港台电影研究[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