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一丹新作寫家書:記錄的意義,后人看得更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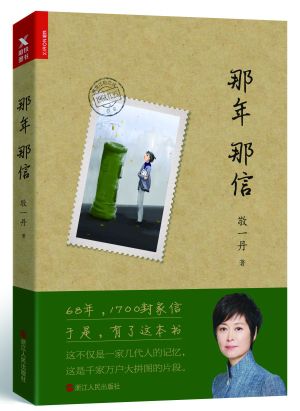



攜新書《那年 那信》與讀者見面
68年時光,1700封珍藏家書,承載了五代人的痕跡。近日,著名主持人敬一丹攜新書《那年 那信》走進北京大學,展開一場別開生面的新書分享會。其作由磨鐵圖書傾力推出,書中敬一丹以“信中信”的方式與四世同堂大家庭的后代交流,引出“信”的故事。從1950年的情書,到2018年的“微信控”,在她看來,這些信裡記錄的不僅是一個家庭的故事,千家萬戶的故事就像一塊塊小拼圖,拼出了不同年代的世間圖景。活動中,敬一丹分享了編寫中的溫情悲喜和家教家風的傳承,此外,好友朱軍、白岩鬆也到場分享各自與“信”的情緣。在接受北京晨報記者採訪時,敬一丹表示,不想忘記,也不想讓女兒不知,這平常的願望使得她創作此書,“這本書是一個接力,要傳給年輕的一代人。我覺得對於記錄的意義,后人會看得更清楚。”
■創作心路
寫這本書是不想忘
敬一丹生於1955年,父母從事法律工作,父母的愛情和人生追求有著濃厚的時代色彩。她小時候就發現,家裡床下有個木箱子,裡邊放著媽媽爸爸的信。這種留存習慣影響了子女后代,家裡的信越來越多,到近年整理時已有1700余封。對比網絡覆蓋、即時通訊的現代,那郵筒上綠色的記憶,那手寫的、穿山涉水歷經寒暑保留下來的信件,絕不僅僅只是一種紀念,更是一種在字裡行間、歲月更迭中的回望。“回望,連接著昨天、今天、明天。” 正如敬一丹所說,記憶與記錄給了我們紀念,記憶是本能,記錄是自覺。
“為什麼寫這本書?我不想忘。”敬一丹說,我們走了那麼多的路,付出那麼多的代價,將來也會老,也會忘記。如果忘了,那不是白走這些路、白付出這些代價了嗎。父母長輩會給我們講故事,但我們有沒有聽過?有沒有聽懂?如果能夠聽懂的話,這些故事就會對我們了解過往的歲月特別感性、真實。對於信的這種文本,敬一丹好像有一種先天性的在意,她回憶,1998年《焦點訪談》最具鋒芒之時,她曾寫了一本書《聲音》就是從成千上萬《焦點訪談》的來信中選取的,寫作時,她就有一種強烈的記錄意識。“我就想,以后的年輕人如果想知道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國老百姓都發出怎樣的聲音,這本書可以提供參照。”不同於那本,此次出版的新書說的是家,是一種柔軟、深情的話題。“當然,這本書也是向我的父母致敬,當媽媽把家信整理成了一本家庭成員看的書時,我們都覺得媽媽太厲害了。同時,媽媽在編寫家信的過程當中,我也知道了我的DNA是怎麼來的,我為什麼也喜歡記錄這些事。”敬一丹稱,母親沒當記者,但她充滿了作為一個記錄者的素質,以至於影響到自己。
給父母做場焦點訪談
《那年 那信》關於記憶、關於回望,更是關於家,書中通過一個個細節傳遞著家教家風的傳承。提起家教家風,小時候的一件事讓敬一丹印象深刻。在她13歲時,父母去外地干校,由她管家裡的瑣事。“一天,媽媽臨時從外地回家,她在廚房忙活,我和以前一樣,在縫紉機前給弟弟們補褲子。一不小心,縫紉機針穿透了我的食指,媽媽見后大聲喊來兩個弟弟:你倆記住,二姐給你們補衣服,手指都扎穿了。她也不比你們大多少,才比大弟大三歲,她就替媽媽爸爸照顧你們……”敬一丹說,假如當年母親把她抱懷裡安慰,她立即就會哭,就會委屈。但母親當時的做法讓她喚起了積極心態,還培養了姐弟之間的手足情深。
敬一丹的家庭是四世同堂,一天,女兒看著奶奶在寫字便問:你還會寫字啊?聽罷敬一丹頓時心中一驚,在孫女眼裡她只是一位在廚房忙活的奶奶。“父母有過的經歷后輩未必知道。所以我跟媽媽說,把你的職業生涯寫寫吧。”在記錄中,她發現父母腦海中很多記憶都在淡漠,於是,敬一丹做了一個決定,給父母做一場焦點訪談。“我寫好了採訪提綱,問我爸,你小時候最愛上什麼學?本來學醫為什麼不學了,去做法律工作了?我的爺爺是什麼樣的人?”說到這些,敬一丹慢慢紅了眼眶,她說,幸好那時採訪了父親,如果再晚些採訪,可能他也會忘記。“進行過很多焦點訪談的採訪,對爸爸和媽媽的採訪是讓我內心最有滿足的。”
■好友分享
朱軍:落筆瞬間一定是真切的
由朱軍主持的《信·中國》是央視推出的讀信欄目,通過電視屏幕將“信”傳遞給廣大觀眾。朱軍認為,今天重提信件就是因為傳媒方式不同,當下快餐文化盛行,碎片化閱讀的年代與我們那時不一樣。“有些時候書信是有用的,那個年代人交流的渠道很單一,我記得當兵時與家裡至少有一兩次的書信來往,我的成長起步與書信有關系。”
“為什麼把文字和信拿出來?因為真的拿起筆寫信時一定通過思量,落筆的一瞬間一定是真切的,而且寫下的文字就是給特指的人看。”朱軍提倡,生日的時候可以給爸爸媽媽寫信,爸爸媽媽生日的時候也可以給他們寫信,到一定的年齡說“我愛你”要寫在紙上。因為對方不光可以感知,多少年后再拿起來更加有意義。“我現在老給我兒子寫信,哪怕給他發短信的時候,我會說‘爸爸愛你’,我說十遍的時候他特別不願意的回一句‘爸爸我也愛你’。”
白岩鬆:了解長輩的歷史才懂得不易
“我坐在這知道專門給我出了一本書,因為我看到第一行字就是68年1700封家信,結果發現是人家父母的信。”白岩鬆幽默地開場說道,借這本書,他希望能夠讓所有年輕人了解自己父母的故事,了解爺爺奶奶的故事,了解一下家族經過了怎樣的千山萬水才那麼有機緣地相遇。
白岩鬆會給每屆他的研究生布置一個作業,就是把他們往上數兩代家人怎麼走在一起的路線圖畫出來。他說,之所以做這樣的作業,因為自己曾做過測試,如今十個年輕人裡有九個能寫出爸爸媽媽的名字,但十個裡卻有九個寫不全爺爺奶奶和姥姥姥爺的名字。“誰能寫得清楚爺爺奶奶怎麼相遇的?姥姥姥爺來時的路是怎樣的?每次學生們都覺得這個作業看似太簡單,回來的時候卻哭著講述作業。因為他們之前不知道長輩那麼艱難,不知道經歷了那麼多的坎坷。”白岩鬆認為,了解國家歷史太大了,把爺爺奶奶、姥姥姥爺到爸媽的地圖畫出來,就有特別重要的價值。
■對話作者
寫給家人的信,把他們都看哭了
北京晨報:您的家庭氛圍,給您的成長帶來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敬一丹:很多事是我人到中年以后才感覺出來的。我第一次跟朋友說我家有一千多封信時,朋友睜大眼睛,非常驚訝,我以為誰家都能這樣呢。而這時才覺得,我是多麼幸運,我父母看重的是什麼,就是這種精神交流、文字記載。
這本書裡有一篇文章,說的是我媽媽后來帶著痛感寫了一件事,就是要跟孩子們說曾經燒掉了家裡的一些照片,以至於所有人對爺爺都沒有印象。媽媽要告訴我們,有些事不要忘記,不是燒掉了,這個人就再也沒有痕跡了。這就是我媽媽對我的影響,她對於一些有價值東西是非常看重的。
北京晨報:您書中給家裡四世同堂寫了信,這些信他們看到了嗎?他們看后有什麼感受?
敬一丹:首先,我把他們都看哭了。其實家裡還有一些三四歲的孩子還看不懂,最后那封信寫給最小的孩子。是說我媽現在變成了微信控,所以我寫道,等你長大的時候,那時可能微信沒了,新的東西又出現了,帶領我們走向更新鮮的空間。其實我寫這本書是一個接力,把我媽媽留下的東西梳理、放大,傳給更年輕的一代。
留下記憶的意義,是受崔永元啟發
北京晨報:能分享一下您現在的生活狀態嗎?
敬一丹:我除了離開《焦點訪談》,其他的也沒離開,《感動中國》我還在主持,已經到了第16次,我希望接下來應該有更年輕的人接替我。其實我退休后,好像挺忙活,還增加了一些新的事兒。比如這種文字表達,讓我找到了很愉快的感覺。我原來說話都是在《焦點訪談》,大家熟悉的樣子,那個時候說話很職業,然而這本新書就更個人化了。
我退休以后寫了三本,這是我的第八本書,這也是最個人的一本書。我沒退休前的五本書都偏重於業務,退休后的三本書都偏重懷舊。《我遇到你》是回顧職業生涯的,《我,末代工農兵學員》是回望青春,《那年 那信》是回望家庭,曾經控制,現在我不加控制地在懷舊。有的時候,回憶是有痛感的,但我不想忘記,也不想讓我女兒不知。
北京晨報:您認為這種個人回憶,對於社會來講,最大的意義在哪兒?
敬一丹:這是真實的、具體的、可感的。說到這一點時,我對我的同事崔永元做口述歷史這個舉動充滿敬意。他做的口述歷史就是為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公眾留下一份記錄。我那時候曾經想,退休后幫他去做口述歷史,那是多有意義的事。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推薦閱讀
相關新聞
- 評論
- 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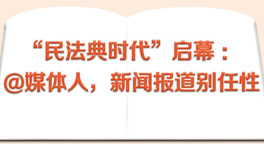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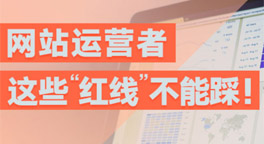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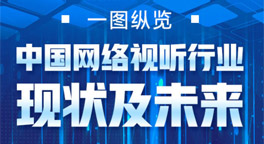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