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播劇《太行山上新愚公》:真人真事“一點不走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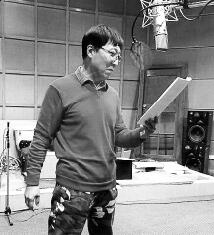
中央實驗話劇院演員韓童生扮演李保國

國家話劇院演員黃小立(左)、 北京人藝演員嚴燕生扮演楊小根、王雙梁。
廣播連續劇《太行山上新愚公》是根據真實故事創作的,真名真姓、真人真事,一點也沒走樣。其主人公河北農業大學教授李保國,正是這樣走過了匆匆而又輝煌的一生。
他35年如一日,埋頭治理荒山,為山區百姓脫貧致富耗盡了畢生的精力。他的課堂不僅在農大明亮的教室,更多的是在山裡的田間地頭。他把最好的論文寫在了太行山上,帶動了369個村的10萬農民脫貧致富。有人算過一筆賬,這些年來他為這些村庄累計增加農業產值35億元,純增收入28.5億元……他走了,留下的不僅是這些,還有那挽著褲腿、腰裡別著大剪刀小鋼鋸跋山涉水的身影,還有那老農民般憨厚淳朴的笑容,自然還有那不盡的悲痛、思念和感動。至於那在他身上閃爍著光芒的新愚公精神,更是會成為太行山百姓世代相傳的集體記憶。
大膽取舍
圍繞新愚公選材
這部廣播劇最為成功之處,就在於生動而藝術地再現了李保國用生命書寫的感人故事,成功地塑造了血肉豐滿、有思想、有靈魂、有情趣和個性的新愚公形象。回望太行,仿佛能看到我們的主人公身影,他如同枝繁葉茂的參天大樹,生機勃勃,根植於大地,聳立於太行之巔。
這首先要歸功於編導的大膽取舍,精心謀劃。35年的風風雨雨,800裡太行的溝溝坎坎,如何取舍?這不能不說是一道難題。
有了!“新愚公”這三個字應該是重中之重的核心內容。它幾乎涵蓋了李保國身上的方方面面,把它作為李保國的稱謂,那是再貼切不過的了。你看,他既有“老愚公”的堅定、堅忍和實干精神,又有經濟頭腦、新的思維和理念﹔既有科學技術和智慧,又有新時期共產黨人的擔當和心系百姓的一腔熱血。別看他整天在深山老林和石頭、果樹為伴,卻的確是新時代的弄潮兒。緊緊圍繞著這三個字選材,突出了重點,也抓住了關鍵,不失為明智的選擇。
另一方面,他們把時間定格在李保國人生道路上的最后幾年,地點則是大山裡的崗底村和青石嶺。一部濃縮了李保國大半生的廣播劇,時間、地點如此集中,這不能不說是主創人員的大膽構想和精心謀劃。編劇任小敏從事廣播劇創作多年,心疼地舍掉了不少東西,但她明白,有舍才有得,隻有精挑細選,再加上高度的集中和藝術概括,才能成為劇,才能達到我們的預期目的。實踐証明,這一步走得很不錯。時間、地點、人物相對集中,這就為結構故事、塑造人物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動靜相濟
人物活起來立起來
為了塑造好“新愚公”形象,音響、動效等手段自不必說,編導主要還在兩個方面下了功夫。一曰動,二曰靜。二者相濟,人物也就立了起來,活了起來。
所謂“動”,主要是指主人公的行動線。劇中李保國出場不俗,剛一露面兒,就趕上了崗底村光棍連鬧事打架,李保國當眾和“光棍連連長”郝大夯簽字畫押——“三年保証他先脫貧,后脫光!”這可是驚人之舉,連村支部書記王雙梁都為他捏著一把汗。開山崩石頭出現了啞炮,他一把推開眾人,獨自奔了過去,還回頭故作輕鬆地說:“深眼悶炮是我發明的、炸藥是我炒制的,我最清楚咋回事。”接下來,指導果樹剪枝、掐花,手是狠了點兒,遭了不少人的白眼和指責,他不惱,笑著說:“秋后見!”有時候好不容易回到河北農大的家,還沒坐穩當,一個告急電話打來,立刻出門,開上他的吉普車,又馬不停蹄地回到山裡。
廣播劇當然沒有畫面,但聽著聽著瞇眼一想,它的畫面感又是那樣的強。那輛破舊的吉普車在山路上時隱時現,那是他在匆匆地趕場救急。他手持大剪刀在果樹下鑽來鑽去,時而和人急赤白臉,時而又是一臉的和善,那是在現場具體指點。他忙起來根本不像個病人,可確實病了,但他卻一直沒有停下來。這個頭戴草帽的黑臉漢子,不知疲倦地奔波著、忙碌著。你放眼望去,在他身后出現的是一片新綠,累累的果實和山民們行進在小康路上的一張張笑臉。
藝術的感染力有時候顯得很神奇。這部廣播劇的篇幅有限,但給我們的感覺卻是:年復一年,35個春秋,李保國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用自己的一招一式、一舉一動實踐著自己的諾言,彰顯著自己的個性,也展示著自己的神採和風貌。
所謂“靜”,指的是主人公的深刻思考和思想表達。要想讓劇中人物活起來,不僅要有事業線、行動線,更重要的還要走進他的內心世界,傳達出他的行為依據和精氣神。
廣播劇是聽覺藝術,不能像小說似的作心理描寫,也不能像視覺藝術那樣,通過演員表演把內心世界外化,他隻能靠話語表達。在這方面,《太行山上新愚公》的編導做得很好,頭一場戲就讓主人公給大家亮了個相。李保國來到崗底,看到鄉親們窮得叮當響,心情沉重得像壓了塊大石頭。他對支書王雙梁說:“這回崗底要是脫不了貧,我李保國決不收兵!”這是他的決心,也是他真情實感的自然流露,從中不難看出他強烈的責任心和使命感。
接下來編導為李保國創造了不少抒發內心世界的機會,那場“夫妻對話”便是突出的一例。那天,他回家搬救兵,山上缺人手,他想讓妻子、兒子同他一起進山。誰不怕自己的孩子輸在起跑線上?誰不知道山裡比城裡苦得多?矛盾沖突是不可避免的。妻子說:“你整天鑽山溝,究竟圖個啥?”李保國說:“人活著,必須記著自己是棵什麼樹,應該結出什麼果……我不為名來,不為利去,半輩子沒給自己撥拉過一粒算盤珠。可我覺得自己很富有:20多項科研成果,30多項實用技術,前南峪已經成為太行山明珠,這樣的人生不也很有價值嗎?”夫妻相對,真實自然。話語雖不多,但沉甸甸的,足以讓你感受到其人格力量。
不過,把他的思想表達推向極致的,還是廣播劇結尾處的“生死對話”。李保國猝然間到了另一個世界。對妻子撕心裂肺的哭喊,他似有回聲:“素萍,我聽見了……今生有你相伴,我很知足!”對兒子的高聲呼喊,他有回應:“兒子,爸不能陪你了……你看山上的樹,石頭越硬,樹根扎得越深。這,才叫男人!”對鄉親們的呼喚,他抬高了聲調:“鄉親們,我知道你們舍不得我,我也舍不得大家,舍不得太行山哪……隻要大伙脫貧致富,那就是我這輩子交出的最好論文!”這超越現實的“生死對話”,讓人動容,催人淚下。它既表達了生者的痛苦、惋惜和懷念,也揭示了李保國豐富的內心世界和共產黨人的胸襟情懷。
說到底,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任務是塑造有時代特色的新人形象。河北廣播電視台精心制作廣播劇《太行山上新愚公》,成功地塑造了新愚公李保國的藝術形象,生動感人。人常說:萬紫千紅才是春,但願有更多的好作品問世。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推薦閱讀
相關新聞
- 評論
- 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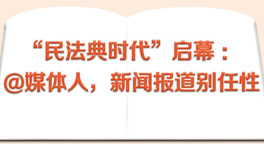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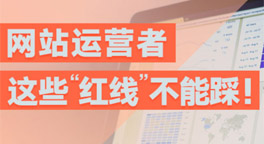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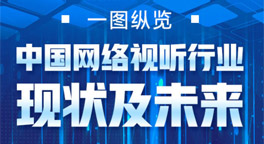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