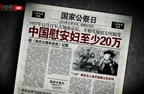傳媒業進入新時期以來,報業在行業改革中始終處於先鋒地位。當始於1980年代的黨報改革很快遇到天花板之后,從晚報到都市報、時尚消費類周報,再到財經類報,每一次報紙形態的演進都較好地彌補了之前報業發育存在的不足。不過,這其中也出現了不少問題。1996年,廣州日報報業集團成立,《廣州日報》成為報業集團的龍頭,不僅表現在輿論場中的強勢地位,還表現為經濟場中的實力。但很可惜,廣州日報報業集團的成功經驗並沒有在全國范圍內擴散,之后組建的報業集團大都回避了類似《廣州日報》在集團內部獨大的組織結構,更多形成“子報養母報”的結構,美其名曰:子報走市場,黨報管輿論。
不過,如果回到1980年代來看,當初實行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的制度設計實屬無奈,主要解決的是辦事業缺少財政支持的問題。但是,經過了30多年的發展,如果盤點我國報業演進的軌跡,常常讓人感慨這是一場“買櫝還珠”式的改革,企業化管理的目標是為了更好地辦好屬於事業性質的報紙,但關於報業的創新成果多集中於企業化經營層面,改革明顯地表現為邊緣突破的特征﹔而關於如何辦好事業性質的報紙這一問題始終停留在改革的起點,幾乎沒有明顯突破。而且,就報業的經營而言,因為有事業單位這個身份的束縛,子報需要反哺母報,大量資金被循環出體外,用於補貼徘徊於市場邊緣的其他報紙,這些子報隻能進行簡單再生產,而無力在更為廣闊的空間參與競爭。這就出現了與經濟學基本常識相違背的現象:一般而言,集團化方式參與市場競爭因為存在交叉補貼會產生優於單個報紙的競爭優勢﹔但恰恰相反,北京青年報、瀟湘晨報、成都商報等在區域市場單打獨斗的報紙卻在市場競爭中表現出明顯優勢。究其原因,這些報紙能夠把掙到的錢用於擴大再生產,而不用擔心被循環到體外。
進入2000年后,新媒體的興起對於報業是一個不小沖擊。如果說1995年到2005年都市報是我國傳媒業的創新領導者,2005年之后,這一地位已經逐步被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取代。我們最早認為報業與互聯網之間的差異僅僅是傳播形態層面上的差異,因此,傳統媒體辦網站被認為是應對互聯網沖擊的關鍵舉措。但是,經過了10年以上反復嘗試,能夠到美國納斯達克上市的互聯網公司幾乎都是非國有背景﹔而具有傳統媒體背景的新媒體公司雖然選擇了在國內上市,但就其業務構成來看,多為WEB1.0時期的技術特征,與這個時代的新媒體業務幾乎格格不入。這時候我們才發現,新媒體絕不僅僅是新在傳播形態,更為深層的是制度層面的優勢﹔尤其那些被美國納斯達克規訓過的新媒體公司,常常具備參與國際競爭的公司治理水准﹔而他們面對的傳統媒體領域卻連基本的市場規則都還沒有確立,例如發行量的認証、廣告收入情況的公開等等。在這樣的格局下,我們看到傳媒業資源的流動主線表現為從傳統媒體向新媒體領域的流動,反向的流動卻很少見到﹔尤其是大量傳媒精英投身到新媒體領域,使得報業創新更加捉襟見肘。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2013年10月28日,原解放日報報業集團和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合並成為上海報業集團,並傳出確立了大舉進軍新媒體領域的戰略方向。筆者認為,這一合並對於打破當前我國報業自從2005年失去創新領導者地位后的僵持局面具有重大意義。我們之前常常寄希望於我國報業在體制層面有所突破﹔而這一次,正是制度設計者主導了集團的合並,使得我們對這次合並在制度層面上的創新充滿期待。
作者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媒介管理學博士﹔復旦大學新聞與傳播學專業碩士學位項目主任。主要研究傳媒產品創新、文化產業政策、新媒體傳播等。先后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3項、省部級項目10項﹔在CSSCI期刊發表論文50余篇。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